第二年,我聽說曉曉懷孕了。是老家的一個遠房親戚告訴我的,說李偉在電話里提了一嘴,喜氣洋洋的。
聽到這個消息,我的心亂了。我要當奶奶了。
那幾天,我晚上翻來覆去地睡不著。腦子裡一會兒是李偉小時候的樣子,一會兒又想像著一個軟軟糯糯的小嬰兒。我甚至跑到商場,在嬰兒用品區逛了半天,看著那些小小的衣服、小小的鞋子,心裡又酸又軟。
可最終,我還是什麼都沒買。
我告訴自己,趙淑蘭,你不能好了傷疤忘了疼。他們既然能自己過,就讓他們自己過去吧。你去湊什麼熱鬧?去了,還不是一樣當牛做馬,最後落不著一句好?
我就這樣,用固執和驕傲,把自己牢牢地困在了原地。
日子就在這種平靜又矛盾的心情中,一天天過去。我漸漸習慣了一個人的生活,習慣了與兒子兒媳的疏離。我以為,我們會一直這樣「相安無事」下去,直到我老得走不動了,或者他們徹底忘了我這個媽。
直到兩年後的那個冬天,李偉的那個電話,打破了所有的平靜。
那天下午,我剛從外面散步回來,在樓下的小攤上買了個烤紅薯。老家的烤紅薯,用的是那種最原始的鐵皮桶,烤出來的紅薯,皮焦肉軟,香氣能飄出半條街。
我捧著熱乎乎的紅薯,慢慢地往樓上走。剛打開門,手機就響了。
是一個陌生的座機號碼。
我猶豫了一下,還是接了。
「喂,是……是趙淑蘭阿姨嗎?」電話那頭的聲音有些陌生,但聽著很年輕。
「我是,你哪位?」
「阿姨,我是李偉的同事。他……他現在在醫院,您能過來一趟嗎?」
我的心「咯噔」一下,手裡的紅薯差點掉在地上:「醫院?李偉怎麼了?他出什麼事了?」
「他……他沒事,就是……就是他愛人,林曉曉的媽媽,今天上午……沒了。曉曉哭得暈過去了,李偉一個人忙不過來,情緒也不太好,所以托我給您打個電話。」
「曉曉她媽……沒了?」我腦子裡「嗡」的一聲,一片空白。
「是,聽說是腎衰竭,沒搶救過來。」
掛了電話,我呆呆地站在玄關,手裡那個滾燙的紅薯,仿佛成了一塊冰,凍得我指尖發麻。
曉曉她媽,那個我只在他們結婚時見過一面的、瘦弱而沉默的女人,就這麼走了?
我的腦海里,不受控制地回想起了兩年前的那場爭吵。
李偉說,她媽媽得了腎病,每個星期都要做透析。
曉曉說,那是她做女兒的責任。
而我說了什麼?
我說她是「白眼狼」,說她「拿著我的錢去盡她的孝心」。
那些刻薄的話,像一把把生了銹的刀子,在時隔兩年之後,又重新開始一刀一刀地割我的心。

我突然意識到,當曉曉每個月從自己微薄的工資里,艱難地擠出那四千塊錢,寄給她那個在病榻上掙扎的母親時,她的心裡,該是何等的煎熬與無助。
而我,在她最需要家人支持和理解的時候,卻用最傷人的話,給了她最重的一擊。
我以為我贏了那場爭吵,我守住了我的錢,守住了我的「道理」。可現在我才發現,我輸得一敗塗地。
我輸掉了一個母親對兒媳本該有的寬容,輸掉了一個長輩對晚輩本該有的體恤。
我捧著那個已經有些涼了的紅薯,慢慢地咬了一口。
又甜又軟,可我的眼淚,卻不爭氣地掉了下來,砸在了紅薯皮上。
我錯了。
我真的錯了。
第66章 一場遲到了兩年的和解
我幾乎是立刻就動身了。
我什麼都沒收拾,就穿著身上的舊棉襖,抓起錢包和手機就衝出了門。我趕到車站,買了最快一班去市裡的大巴。
四個小時的車程,我如坐針氈。窗外的景色飛速掠過,我的心裡卻像是在放慢鏡頭,一遍遍地回放著過去的一切。我的固執,我的刻薄,我的自以為是,在這一刻,都成了審判我的罪證。
我終於明白,曉曉當初的隱瞞,不是不信任,而是一種卑微的自尊。她怕被我看輕,怕我以為她嫁給李偉,就是圖我們家的錢來給她媽治病。她想用自己瘦弱的肩膀,扛起那份如山的責任,不給任何人添麻煩。
是我,用我那套狹隘的、斤斤計較的價值觀,去揣度了一個女兒的孝心。
車到站時,天已經黑了。我按照李偉同事發來的地址,打車直奔醫院。
在醫院的走廊里,我看到了李偉。
兩年不見,他瘦了,也憔悴了,眼窩深陷,下巴上全是青色的胡茬。他靠在牆上,雙眼無神地望著天花板,像一尊被抽走了靈魂的雕塑。
看到我,他猛地站直了身體,眼睛瞬間就紅了,嘴唇哆嗦著,半天說不出一句話,只是沙啞地喊了一聲:「媽……」
我快步走過去,一把抱住他。
這個快三十歲的男人,在我的懷裡,哭得像個孩子。他所有的委屈、壓力和悲傷,在這一刻,終於找到了一個可以釋放的出口。
「媽,我對不起您……我沒用……我沒照顧好曉曉……」他斷斷續續地說著。
我拍著他的背,眼淚也止不住地流:「傻孩子,不怪你,都怪媽……是媽不好,是媽太犟了。」
我們母子倆,在醫院冰冷的走廊里,相擁而泣。那道隔閡了我們兩年的牆,在這一刻,終於轟然倒塌。
哭了好一會兒,李偉的情緒才稍微平復下來。他告訴我,曉曉的媽媽是今天上午走的,走的時候很安詳。曉曉一直守在旁邊,親家母一走,她那根緊繃著的弦就斷了,哭得暈了過去,現在還在病房裡打著點滴。
我跟著李偉,輕手輕腳地走進病房。
曉曉躺在病床上,臉色蒼白得沒有一絲血色,眼角還掛著淚痕。她的肚子已經微微隆起,顯然,我那個未曾謀面的孫子或孫女,正在她的身體里安睡。
看著她這副樣子,我的心像被一隻手狠狠地攥住了,疼得喘不過氣來。
我走過去,在床邊的椅子上坐下,輕輕地握住她那隻沒有打點滴的手。她的手很涼,像一塊冰。
也許是感覺到了我手心的溫度,她的眼睫毛顫動了一下,緩緩地睜開了眼睛。
當她看到是我時,空洞的眼神里,閃過一絲驚訝,隨即,眼淚又涌了出來。
「媽……」她開口,聲音微弱得像蚊子叫。
「欸,曉曉,媽在呢。」我趕緊應聲,用另一隻手笨拙地幫她擦去眼淚,「別哭,別哭壞了身子。你肚子裡,還懷著孩子呢。」
她看著我,眼淚流得更凶了,卻只是搖著頭,一個勁兒地說:「媽,對不起……我媽……我媽臨走前還念叨,說對不起您,給您添麻煩了……」
「胡說!說什麼傻話呢!」我打斷她,聲音也哽咽了,「該說對不起的人是我!是我小心眼,是我混蛋!是我沒能體諒你的難處,還說了那麼多傷你心的話。曉曉,是媽對不起你。」
我把兩年前就該說的道歉,在這一刻,鄭重地說了出來。
曉曉哭著搖了搖頭,她反手握住我的手,握得很緊。
我們倆,一個躺在病床上,一個坐在床邊,就這樣握著手,默默地流著淚。沒有更多的言語,但我們都知道,我們之間所有的心結,在這一刻,都解開了。
後來,我留了下來,幫著李偉和曉曉處理親家母的後事。
我這才知道,這兩年,他們過得有多難。
我斷了月供之後,他們每個月要還五千的房貸,還要承擔曉曉媽媽四千的醫藥費,加起來就是九千的硬性支出。他們倆的工資,除了這些,剩下的也就只夠最基本的生活。
李偉為了多賺錢,下班後還偷偷去接私活,經常畫圖畫到凌晨兩三點。曉曉為了省錢,幾乎沒買過一件新衣服,每天中午都是自己從家裡帶飯。
可即便這樣,他們也從來沒有在我面前,提過一個「錢」字。
李偉跟我說:「媽,我們知道您當初走,是心裡有氣。我們不想再因為錢的事,讓您更煩心。我們想著,我們年輕,苦一點,熬一熬,總能過去的。」
我聽著,心裡又是一陣酸楚。
我以為我的離開是成全了自己,卻沒想到,是把所有的重擔,都壓在了我最愛的兩個人身上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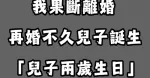
 武巧輝 • 3K次觀看
武巧輝 • 3K次觀看
 楓葉飛 • 2K次觀看
楓葉飛 • 2K次觀看









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