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文博,」我深吸一口氣,讓自己的聲音保持平穩,「我已經說過了,我回不去。如果外賣不合胃口,你們可以自己做,冰箱裡不是有菜嗎?或者再點一份別的。就這樣,我還要忙,掛了。」
我掛斷電話,把這個號碼拉黑。
我知道,今晚的攤牌,已經不可避免。我不能再躲下去了。有些話,必須當著所有人的面,清清楚楚地說出來。
我穿上新買的大衣,結了帳,打車回家。
當我用鑰匙打開家門時,迎接我的不是新年的喜慶,而是一屋子凝重到幾乎結冰的空氣。
客廳的燈光慘白,電視里春晚的歌舞聲顯得格外刺耳。我媽、舅舅、舅媽,還有表弟文博,四個人齊刷刷地坐在沙發上,誰也不說話。餐桌上,擺著幾個外賣餐盒,裡面的菜動了幾筷子,幾乎還是滿的。
看到我進來,我媽「霍」地一下從沙發上站起來,眼睛通紅,指著我的鼻子,聲音都在發抖:「你還知道回來?!」
舅舅趕緊拉住她,打著圓場:「秀琴,你少說兩句。嵐嵐,快過來,外面冷吧?」
我沒有理會舅舅的「好意」。我脫下大衣,把它平整地搭在玄關的衣架上,然後換上拖鞋,一步一步走到他們面前。
我環視了一圈,目光從我媽憤怒的臉,到舅舅尷尬的笑,再到舅媽王麗略帶審視的表情,最後落在一臉無所謂、低頭玩手機的表弟身上。
「為什麼不吃?」我指了指桌上的外賣,平靜地問。
「這東西能吃嗎?」我媽搶著說,「冷冰冰的,一點年味都沒有!你就是故意的是不是?故意讓你舅舅一家看我們家的笑話!」
「年味?」我笑了,笑意卻未達眼底,「媽,你所謂的年味,就是我一個人在廚房裡忙得腳不沾地,而你們全家人在客廳里歡聲笑語嗎?就是我累得年夜飯都吃不下幾口,你們酒足飯飽後剔著牙,說一句『辛苦了』嗎?」
我的聲音不大,但每一個字都像釘子,敲在客廳的寂靜里。
「十年了,」我看著我媽,一字一句地說,「從我二十二歲到三十二歲,整整十年。每年的除夕,我都是在廚房裡過的。你們誰問過我一句,累不累?誰問過我一句,想不想吃點自己喜歡的?沒有。」
「我發燒的時候,你們讓我扛一扛。我被燙傷的時候,你先關心的是表弟有沒有被嚇到。我提出出去吃,你說浪費錢,說舅舅不喜歡。我只是想休息一下,你就讓我滾出這個家。」
我的目光轉向舅舅趙國強:「舅舅,你說你最愛吃我做的『全家福砂鍋』。你知道那道菜有多麻煩嗎?要提前三天泡發海參、花膠,要用老母雞和火腿吊四個小時的高湯,要把十幾種食材分別處理,最後再一層層碼好,小火慢燉。每一年,光是準備這一道菜,就要花掉我兩天的時間。」
舅舅的臉色一陣紅一陣白,張了張嘴,沒說出話來。
我又看向舅媽王麗:「舅媽,你說我媽有福氣。是的,她是有福氣,因為她有一個可以被無限壓榨的女兒。每年你們來,就像來視察的貴賓,什麼都不用做,張口就能吃飯,吃完碗一推,就可以去看電視、去打牌。你們有沒有想過,那些碗,是誰在數九寒冬里,一個個洗乾淨的?」

王麗的頭低了下去,臉頰微微發燙。
最後,我看著還在玩手機的趙文博:「文博,你打電話讓我回去做飯。在你眼裡,我這個表姐,是不是就是一個會做飯的工具人?你從來沒有把我當成一個也需要休息、需要被尊重的家人。」
趙文博被我點名,終於抬起頭,眼神里有些錯愕和不服氣,但終究沒敢吭聲。
整個客廳,死一般的寂靜。只有電視里還在不知疲倦地唱著「難忘今宵」。
「我不是不想招待你們,我只是不想再用這種不公平的方式來維持所謂的親情。」我看著他們,感覺積壓了十年的委屈和憤怒,在這一刻終於找到了出口,說完之後,整個人都輕鬆了。
「如果親情意味著一個人無休止的犧牲和另外一群人的心安理得,那這樣的親情,我寧可不要。」
第5章 塵封的往事
我的話像一塊巨石,投入平靜的湖面,激起了千層浪。
最先崩潰的是我媽。
她像是被抽走了所有力氣,一下子跌坐回沙發上,捂著臉,發出了壓抑的哭聲。那哭聲里,有憤怒,有委屈,但更多的是一種我從未聽過的,深深的無助。
「我……我也不想的啊……」她哽咽著,斷斷續續地說,「我能怎麼辦……」
舅舅趙國強的臉色難看到了極點。他站起來,又坐下,搓著手,一副坐立難安的樣子。他看著我,嘴唇囁嚅了半天,才終於擠出一句話:「嵐嵐,舅舅……舅舅對不起你。我們……我們都沒想到,會給你這麼大的壓力。我們以為……以為你喜歡做這些……」
「喜歡?」我自嘲地笑了笑,「誰會喜歡把自己累得像條狗一樣,來換取別人廉價的誇獎?舅舅,你也是有女兒的人,如果你的女兒在婆家,每年都是這樣過年,你會怎麼想?」
舅舅的臉瞬間漲成了豬肝色,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
一直沉默的舅媽王麗,這時卻站了起來。她走到我身邊,拉了拉我的胳膊,低聲說:「嵐嵐,別說了。……她心裡苦。」
說著,她嘆了口氣,看了一眼還在哭泣的趙秀琴,又看了一眼窘迫的丈夫,像是下定了什麼決心。
「其實,有些事,一直瞞著你。」王麗緩緩開口,「你總覺得偏心你舅舅,什麼都向著我們。其實……她是心裡有愧啊。」
我愣住了,不解地看著她。
「你外公外婆走得早,那時候十幾歲,你舅舅才七八歲。家裡窮得叮噹響,姐弟倆相依為命。」王麗的聲音很輕,像是在講述一個遙遠的故事,「有一年冬天,你舅舅生了場大病,高燒不退,眼看就要不行了。家裡一分錢都沒有,半夜三更,冒著大雪,一家家去敲門借錢,跪在地上求人家。最後,是村裡的一個赤腳醫生,看她們可憐,賒了藥,才把你舅舅從鬼門關拉了回來。」
「但那場病,把你舅舅的身體徹底搞垮了。醫生說,底子壞了,以後幹不了重活。從那時候起,就發了誓,這輩子,只要她有一口飯吃,就絕對不會讓你舅舅再受一點苦,受一點委屈。」
我的心,像是被什麼東西狠狠地揪了一下。這些事,我媽從來沒有跟我說過。在我印象里,她總是堅強、能幹,像個無所不能的女超人。我從不知道,她有過那樣絕望和卑微的過去。
「後來,嫁給了你爸,條件好點了,更是把所有的虧欠都想補回來。你爸是個老好人,也支持她。再後來,你爸走了……」王麗頓了頓,聲音更低了,「覺得,這個家裡,能指望的男人,就只剩下你舅舅了。她怕啊,怕我們不管你們娘倆,所以才拼了命地對我們好,想把我們牢牢地拴在這個家裡。」
「她不是不心疼你,嵐嵐。」王麗的眼圈也紅了,「她每次看你在廚房裡忙,嘴上不說,回頭就跟我念叨,說看你累得都瘦了,她心裡難受。可她就是轉不過那個彎兒來,她覺得,只要讓你舅舅一家吃好了,滿意了,我們這個家,才算有個依靠,才不會散。」
原來是這樣。
我看著沙發上那個哭得像個孩子的母親,所有的憤怒和怨恨,在這一瞬間,都開始慢慢消解。
我怨的,是她的不公,是她的理所當然。但我不知道,在這份不公的背後,藏著一個姐姐對弟弟沉重的誓言,藏著一個中年喪偶的女人,對未來深深的恐懼和不安。
她不是不愛我,她只是用了一種錯誤的方式,一種傷害了我,也困住了她自己的方式,來維繫她心中那個脆弱的「家」。
客廳里,一片死寂,只有我媽壓抑的抽泣聲。
一直低著頭的舅舅趙國強,猛地站了起來。他走到我媽面前,「噗通」一聲,竟然跪了下去。
「姐!」他一個四十多歲的男人,哭得涕淚橫流,「姐,我對不起你!是我沒出息,這麼多年,一直讓你操心,還拖累了嵐嵐……我不是人!」
這個變故,讓所有人都驚呆了。
我媽也忘了哭,手忙腳亂地去拉他:「國強,你這是幹什麼!快起來!快起來!」
「我不起來!」舅舅固執地跪在地上,仰著頭,滿臉淚水,「姐,這些年,你為我做的夠多了。以後,該我來照顧你了。嵐嵐說得對,我們不能再這麼心安理得地把你和孩子的付出當成應該的了。我們……我們不是來做客的,我們是一家人啊!」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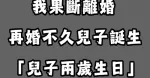
 武巧輝 • 3K次觀看
武巧輝 • 3K次觀看
 楓葉飛 • 2K次觀看
楓葉飛 • 2K次觀看









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