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媽要把舅舅一家接來過年,卻讓我一個人做飯,今年我不慣著她了
當我最終解下那條洗得發白、邊緣起了毛的舊圍裙,把它整整齊齊疊好,放在空無一物的冰冷灶台上時,我媽和舅舅一家人,正呆若木雞地站在我身後,看著滿地沒動過的菜,和一桌子冰冷的碗碟。
那一天,是除夕。
整整十年,從我大學畢業那年算起,每年的這頓年夜飯,都是我一個人的戰場。十年,三千六百多個日夜的付出與忍耐,都在那個瞬間,隨著我轉身的動作,畫上了一個決絕的句號。
而這一切,都要從半個月前,我媽打來的那個電話說起。
第1章 熟悉的電話
「嵐嵐,你舅舅他們今年還跟往年一樣,二十九過來,住到初五再走。」
電話那頭,我媽趙秀琴的聲音一如既往地輕快,帶著一種不容置喙的熟稔。仿佛這不是一個商量,而是一個早已寫入家庭憲法的年度通知。
我正對著電腦螢幕核對一份季度報表,密密麻麻的數字看得我眼睛發酸。聽到「舅舅」兩個字,我的太陽穴不自覺地跳了一下。我捏了捏鼻樑,儘量讓自己的聲音聽起來平靜:「哦,知道了,媽。」
「那你這兩天抽空把家裡大掃除一下,特別是客房,被褥都拿出去曬曬,別讓人家覺得我們家邋遢。」她繼續吩咐著,語氣自然得像是在安排自家女兒周末回家吃飯。
「嗯。」我含糊地應著。
「還有,你舅舅點名要吃你做的那個『全家福砂鍋』,說想了一年了。你表弟文博呢,想吃可樂雞翅和糖醋裡脊。至於你舅媽……她那個人不挑,隨便做兩個清淡的就行。菜單你提前列一下,別到時候手忙腳亂。」
電話里的聲音還在絮絮叨叨,我的思緒卻已經飄遠了。
我的舅舅趙國強,是我媽唯一的弟弟。從小,我就聽我媽念叨,說外公外婆走得早,她作為長姐,拉扯弟弟長大吃了多少苦。這份「長姐如母」的恩情,似乎成了我媽一輩子還不完的債,也順理成章地,成了我必須背負的責任。
自我爸前些年因病去世後,媽就把對弟弟的「補償」心理發揮到了極致。尤其是過年,我們這個小家,仿佛成了舅舅一家的專屬度假村和私房菜館。
記憶里的第一個「戰場」是在我二十二歲那年。剛畢業,工作還沒完全上手,就被我媽一通電話叫回家,理由是:「你舅舅一家要來過年,家裡缺個做飯的。」
那時候的我,單純地以為這就是親情。我滿懷熱情地扎進廚房,從擇菜、清洗、切配到煎炒烹炸,一個人從早忙到晚。當滿滿一桌二十多道菜端上桌時,我累得腰都直不起來,兩隻手被冰水和熱油折磨得通紅。
飯桌上,舅舅趙國強喝得滿臉紅光,拍著我的肩膀大聲誇讚:「我們家嵐嵐就是能幹!這手藝,比外面大飯店的廚子還強!」
表弟趙文博嘴裡塞滿了可樂雞翅,含糊不清地附和:「姐,你做的菜最好吃了!」
舅媽王麗則笑著對我媽說:「姐,你真有福氣,養了這麼個好女兒。」
而我媽,趙秀琴女士,臉上洋溢著無比的自豪和滿足,仿佛這滿桌的菜是她自己做的,仿佛女兒的辛勞是她可以向弟弟炫耀的資本。她夾起一塊最大的排骨放進舅舅碗里,嘴裡說著:「喜歡吃就多吃點,讓你姐給你做!自家外甥女,還能差了你的?」
那一刻,所有人都在笑,只有我,端著飯碗,在廚房的油煙味和客廳的歡笑聲之間,第一次感到了某種難以言說的隔閡。我好像不是這個家的女兒,而是一個被臨時請來、只負責提供服務的廚娘。
這種感覺,在接下來的十年里,被反覆印證,逐年加深。
每一年,舅舅一家來的時間越來越長,點的菜越來越複雜,而我媽對我提的要求,也越來越理所當然。從最初的年夜飯,發展到承包他們從年二十九到初五的一日三餐,外加各種零食點心。
我不是沒有過微詞。有一年,我實在累得病倒了,年三十還在發著低燒。我跟我媽說,能不能今年簡單點,或者讓舅舅舅媽也搭把手。
我媽當時正在給舅舅泡茶,頭也沒抬地說:「你舅媽那手藝,國強吃不慣。你表弟正是長身體的時候,能湊合嗎?你年輕,扛一扛就過去了,別那麼嬌氣。」
舅舅在旁邊聽到了,也笑呵呵地打圓場:「嵐嵐就是我們家的御用大廚,別人替代不了!」
那一瞬間,我心裡的委屈像是被堵住的洪水,找不到出口。在他們眼裡,我的付出是應該的,我的勞累是「年輕」和「嬌氣」,我的感受,無足輕重。
而我,總是那個不懂拒絕的「好孩子」。我怕我媽為難,怕所謂的親情出現裂痕,怕被扣上「不懂事」的帽子。於是,我年復一年地忍了下去。
直到今年。
「……嵐嵐?嵐嵐?你在聽嗎?」電話里,我媽的聲音把我拉回現實。
我深吸一口氣,報表上的數字在眼前晃動,變成了舅舅、舅媽、表弟一張張理所當然的臉。十年了,我的青春、我的假期、我的新年,都耗費在了那一方小小的廚房裡。我換來了什麼?是家人的體諒和心疼嗎?不,是變本加厲的索取和習以為常的輕視。
「在聽。」我緩緩開口,聲音裡帶著一絲自己都未曾察覺的疲憊和冰冷,「媽,今年,我不想做飯了。」
電話那頭,我媽那連珠炮似的安排戛然而止。
短暫的沉默後,是她拔高了八度的、難以置信的質問:「你說什麼?!」
我知道,今年的這個年,註定不會平靜了。
第2章 第一次反抗
「林嵐,你再說一遍?」我媽的聲音隔著聽筒都透著一股寒氣,連名帶姓地叫我,是她真正生氣的徵兆。
我閉上眼睛,仿佛能看到她此刻緊皺的眉頭和緊抿的嘴唇。放在往常,我可能已經心軟,開始找補了,會說「我不是那個意思」、「我就是太累了隨口一說」。但這一次,胸口那股鬱結了十年的悶氣,像一堵牆,頂住了我所有退縮的念頭。
「我說,媽,今年過年,我不想再一個人做那麼多菜了。我工作也很累,我也想好好歇歇,過個年。」我的語氣很平靜,但每一個字都咬得很清楚。
「你累?誰不累?我養你這麼大我累不累?」我媽的經典詰問立刻就來了,「你舅舅一家一年就來這麼一回,你做幾頓飯怎麼了?你小時候,你舅舅是怎麼疼你的,你都忘了?給你買的零食,給你買的玩具,你現在出息了,能掙錢了,就不認人了?」
我感到一陣無力。那些所謂的「疼愛」,不過是舅舅偶爾來串門時,順手從街邊小賣部買的兩包零食,一件不超過二十塊錢的塑料玩具。這些微不足道的付出,卻成了我媽口中我必須湧泉相報的恩情。而我十年如一日的年夜飯,在她看來,只是「幾頓飯」而已。
「媽,這不是一回事。」我試圖跟她講道理,「我不是不招待舅舅,但不能所有事情都壓在我一個人身上。我也是這個家的一分子,不是專門伺候人的保姆。」
「保姆?!」這個詞顯然刺痛了她,「我讓你給你親舅舅做頓飯,你就說自己是保姆?林嵐,你太讓我失望了!你是不是覺得你爸不在了,這個家就沒人管得了你了?你翅膀硬了是不是?」
電話那頭傳來了劇烈的喘息聲,我知道她氣得不輕。我的心也揪著疼,我不想跟她吵,我比誰都希望她能開心。可是一想到那間廚房,想到那無休無止的油煙和洗不完的碗,我就覺得窒息。
「我沒有那個意思,」我放緩了語氣,「媽,要不這樣,今年我們出去吃吧?我來訂餐廳,找個好點的,大家輕輕鬆鬆過個年,不好嗎?」
這是我能想到的最好的折中方案。
「出去吃?你知道你舅舅那個人,就喜歡在家裡吃,覺得外麵館子不幹凈,也沒年味兒!」我媽想也不想就否決了,「再說了,外面吃多貴啊?一家子人,一頓飯不得上千?你有那閒錢,還不如給你表弟包個大紅包!」
我徹底說不出話了。原來,在她心裡,我的時間和精力,是如此廉價,甚至比不上一頓飯錢。而我辛苦掙來的錢,也應該優先滿足她的娘家人。
「行了,我不想跟你吵。」我媽似乎也覺得再說下去沒有意義,用一種不容商量的語氣做了總結,「這事就這麼定了。你這兩天把脾氣收一收,別等你舅舅來了還給我甩臉子。你要是真不想做,行,你現在就從這個家搬出去,以後別回來了!」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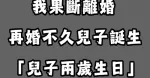
 武巧輝 • 3K次觀看
武巧輝 • 3K次觀看
 楓葉飛 • 2K次觀看
楓葉飛 • 2K次觀看









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