她不敢看陽台那個角落,仿佛那裡盤踞著一條吐著信子的毒蛇。夜裡稍微一點風吹草動,她都會驚跳起來,冷汗浸透單薄的秋衣,心在腔子裡擂鼓般狂跳,耳朵里全是血液奔流的轟鳴。
她死死攥著被角,指關節捏得發白,生怕下一秒兒子憤怒的咆哮或者兒媳更惡毒的咒罵就會破門而入。
可奇怪的是,日子一天天過去,預想中的風暴並未降臨。
王艷依舊刻薄,罵聲依舊尖銳刺耳,但內容翻來覆去,還是那些「老廢物」、「吃白食」、「早點死」的陳詞濫調,並未沾染半分「錢」的字眼。
李建國打回來的電話,依舊是隔著千山萬水、透過冰冷電流傳來的敷衍:「媽,身體還好吧?我最近項目緊,特別忙,過陣子,過陣子一定抽空回去看你……艷艷?
她脾氣就那樣,您多擔待,別跟她一般見識……錢?您放心,夠用就行,不夠跟我說……」
那語氣里的疲憊和心不在焉,像一層厚厚的灰塵,覆蓋了李桂芳心裡殘存的那點微末希望。
兒子似乎……根本不知道那張存單的存在?這個念頭像野草一樣在她荒蕪的心田裡瘋長。也許,他早就忘了?忘了當年他媽是賣了唯一的窩才湊夠他留學的天文數字?忘了臨行前信誓旦旦的承諾?
巨大的悲涼像一塊巨石,沉甸甸地壓在胸口,讓她喘不過氣。
那357萬的灰燼,燒掉的不僅是錢,更像是燒斷了她和兒子之間最後那根無形的、維繫著親情的絲線。
空,前所未有的空。這感覺甚至蓋過了最初的恐懼。
她變得異常沉默,像一尊會移動的泥塑。除了必要的應答,幾乎不再開口。
王艷罵她,她就聽著,渾濁的眼睛望著窗外某個虛空點,仿佛那些惡毒的語言只是穿過空氣的風。兒媳讓她做什麼,她就拖著沉重的腿腳去做,動作遲緩得像慢放的電影。
她不再去陽台整理那些廢品,任由它們堆在那裡,散發的氣息和這屋子裡的絕望一樣,日漸陳腐。

身體里的疼痛卻不會因此放過她。那深入骨髓的風濕痛變本加厲,像無數細小的冰錐,日日夜夜在關節縫隙里鑽鑿。
抽屜里的止痛藥瓶空得越來越多。每次去買那最便宜的藥片,經過銀行那光潔明亮的大理石外牆,她都會下意識地加快腳步,心臟像被一隻無形的手攥緊。
玻璃幕牆映出她佝僂、灰敗的影子,像個移動的、被生活徹底榨乾的殘骸。
有一次,她甚至在裡面看到一張模糊的、帶著詭異平靜的臉——那是她自己嗎?她不敢細看,倉皇低下頭匆匆逃開。
偶爾,在死水般的沉寂里,會有一絲極其微弱的聲音從心底最深處鑽出來,像黑暗中一點將熄未熄的星火:燒了……也好。
燒了,就乾淨了。燒了,就……自由了?這念頭讓她自己都感到一陣心驚肉跳的寒意和解脫般的眩暈。
她趕緊搖搖頭,像是要甩掉什麼大逆不道的想法,重新把自己埋進那無邊的麻木里。
時間在壓抑中艱難地爬行。日曆無聲地翻過了一頁又一頁。窗外的梧桐樹葉,從深綠到枯黃,再到被寒風卷著打旋落下,鋪滿了樓下冰冷的水泥地。
一個月,整整三十個日夜交替,就在這種令人窒息的沉默和等待中,過去了。
那天傍晚,天色陰沉得像一塊髒兮兮的舊鉛皮,壓得人喘不過氣。寒風從窗縫裡鑽進來,帶著尖利的哨音,屋裡比屋外還冷幾分。
李桂芳裹著那件穿了不知多少年、早已洗得發硬變薄的舊棉襖,縮在客廳那張吱呀作響的單人沙發里,手裡抱著一個早已涼透的鹽水瓶暖手。
她眼神空洞地望著對面牆上那幅積滿灰塵的舊掛曆,上面印著一個咧嘴傻笑的胖娃娃。王艷歪在長沙發上刷手機,螢幕幽藍的光映著她那張濃妝也蓋不住戾氣的臉。
屋裡只有手機短視頻外放出的誇張笑聲和罐頭掌聲,空洞地迴響著,更添了幾分寂寥和冰冷。
突然,「砰」地一聲悶響!
老舊的單元門被用力推開,撞在牆上,震得整個小客廳似乎都晃了一下。冷風卷著樓道里的塵土氣息猛地灌了進來。
一個高大的身影裹挾著室外的寒氣,堵在了門口。是李建國!
他穿著一身挺括的深灰色羊毛大衣,頭髮梳得一絲不苟,臉上帶著一種長途奔波後的疲憊,但那雙眼睛卻異常明亮,嘴角更是抑制不住地向上揚起,形成一個巨大而真實的笑容。
他肩上挎著電腦包,手裡還提著一個印著機場免稅店LOGO的精緻紙袋。
「媽!艷艷!」李建國的聲音洪亮,帶著顯而易見的興奮,瞬間驅散了屋裡的沉悶,「我回來了!提前結束!給你們個驚喜!」他大步跨進來,隨手把行李往地上一放,目光熱切地掃過沙發上的母親和妻子。
王艷像被針扎了屁股一樣,「噌」地從沙發上彈起來,臉上瞬間堆滿了誇張的、甜得發膩的笑容,變臉速度快得令人咋舌:「哎呀!建國!你可算回來了!想死我了!」
她扭著腰肢就撲了過去,聲音嗲得能滴出蜜糖,「怎麼不提前說一聲?我好去機場接你啊!」她伸手就要去接李建國手裡的袋子,眼睛貪婪地往裡面瞄。
李建國笑著躲開她,沒理會妻子的殷勤,目光徑直越過她,帶著久違的暖意和一絲不易察覺的愧疚,牢牢鎖在角落裡那個單薄、僵硬的身影上:「媽!看看兒子給你帶了什麼好東西!」他
語氣輕快,帶著一種急於分享的喜悅,「瑞士的巧克力,還有頂級魚油!對您關節好!」他一邊說,一邊把那個精美的紙袋往李桂芳坐著的沙發扶手上放。
李桂芳的身體在李建國進門的那一刻就完全僵住了。像一截驟然被凍住的枯木。一個月來在心中反覆預演、恐懼、甚至絕望等待的場景,真的發生了。
她渾濁的眼珠艱難地轉動了一下,視線沒有落在兒子臉上那久違的、生動的笑容上,也沒有落在那看起來就價值不菲的禮物上。
她的目光,帶著一種近乎宿命般的死寂,緩緩地、緩緩地,移向了自己面前那張蒙著廉價塑料布的四方小茶几。
李建國的笑容還掛在臉上,順著母親那異常直勾勾、毫無生氣的目光,下意識地也看了過去。
就在沙發扶手旁邊,那張布滿劃痕和茶漬的小茶几上,靠近邊緣的地方,放著一個敞口的舊搪瓷碗。
碗底,赫然是一小堆灰黑色的、帶著焦糊邊緣的紙灰!它們鬆散地堆疊著,幾片較大的殘骸還能勉強看出紙張燃燒後蜷曲的形狀,像某種不詳的、來自另一個世界的祭品。
其中一小片灰燼的邊緣,一個被烈焰燎得只剩下一半、筆畫扭曲的「叄」字,如同一個猙獰的傷口,冷冷地、無聲地暴露在空氣里。
時間,仿佛在這一刻被徹底凍住了。
李建國臉上的笑容,像烈日下的劣質油漆,先是凝固,隨即以肉眼可見的速度開始剝落、碎裂。
那明亮的眼神迅速被一種巨大的茫然和難以置信的驚愕所取代。他嘴角揚起的弧度還沒來得及收回,就那樣僵硬地定格在臉上,顯得極其怪異。
「這……」他喉結上下滾動了一下,發出一個乾澀的單音,目光死死釘在那堆灰燼上,又猛地轉向母親那張毫無血色的臉,「媽……這……什麼東西?」
王艷也看到了。她臉上的媚笑瞬間消失,被一種混合著驚疑和本能厭惡的表情取代。
她撇了撇嘴,嫌惡地掃了一眼那堆髒兮兮的灰燼:「誰知道這老東西又搞什麼鬼!整天神神叨叨的,盡弄些髒東西回來!我說過多少次了,別把這些破爛放桌上,晦氣!」
她說著,習慣性地伸出手,就要去抓那個搪瓷碗,想把這礙眼的東西丟掉。
「別動!」
李桂芳沙啞、乾澀、帶著破風箱般嘶啞的聲音猛地響起,像生鏽的鐵片刮過玻璃。聲音不大,卻帶著一種從未有過的、令人心悸的決絕力量。
王艷的手僵在半空,被這突如其來的呵斥嚇了一跳。

她難以置信地瞪大眼睛,看著角落裡那個一向逆來順受、連大氣都不敢喘的婆婆:「你吼我?老東西你反了天了?敢吼我?一堆垃圾還不讓扔?」她尖聲叫起來,塗著鮮紅指甲油的手指幾乎戳到李桂芳的鼻尖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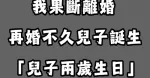
 武巧輝 • 4K次觀看
武巧輝 • 4K次觀看
 楓葉飛 • 2K次觀看
楓葉飛 • 2K次觀看









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