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給何晴發了條信息:錢轉過去了,快去給孩子辦手續吧。一切都會好起來的。
很快,她回了信息,只有短短几個字,卻顯得無比沉重:舒文,大恩不言謝。
晚上回到家,趙鵬已經做好了飯。他看到我,臉色有些複雜,欲言又止。
我主動開口,語氣平靜但堅定:「趙鵬,錢我已經轉給何晴了。」
他愣住了,手裡的碗差點沒拿穩。他看著我,眼神里有震驚,有失望,最終都化為一聲無奈的嘆息。
「林舒文,你真是……」他搖了搖頭,沒再說什麼,只是默默地坐下吃飯。
那頓飯,我們吃得異常沉默。我知道,我這個先斬後奏的決定,深深地傷害了他。這不僅僅是錢的問題,更是對他信任的踐踏。但我當時堅信,時間會證明我是對的。等樂樂康復了,何晴把錢還回來,趙鵬就會理解我今天的決定。
接下來的幾天,我試著聯繫何晴,想問問樂樂的情況。
第一天,我給她發信息:樂樂進倉了嗎?一切順利嗎?
她回:嗯,剛安排好,謝謝你,舒文。
第二天,我打電話給她,想聽聽她的聲音。電話響了很久,被掛斷了。過了一會兒,她回了條簡訊:在無菌病房外,不方便接電話,有事微信說。
我覺得很正常,醫院裡肯定規矩多,也就沒多想。
第三天,我又發信息問:孩子情況怎麼樣?有什麼需要幫忙的隨時開口。
這一次,信息石沉大海,再也沒有回覆。
第四天,我再打電話,聽到的已經是「您撥打的電話已關機」。
我的心,開始一點點往下沉。一種不祥的預感,像藤蔓一樣,慢慢爬上我的脊背。我安慰自己,她可能太忙了,手機沒電了,在照顧孩子,沒時間顧及其他。
可是一連一個星期,她的手機都是關機狀態。微信不回,QQ頭像也是灰色的。
我徹底慌了。
我跟公司請了假,按照記憶中的地址,找到了她家的那個老小區。敲了半天門,裡面毫無動靜。隔壁一個正在擇菜的大媽探出頭來,好奇地問我找誰。
「阿姨,我找住這家的何晴,您知道他們去哪兒了嗎?」
「何晴?」大媽皺著眉想了想,「哦,你說那家啊。他們上個禮拜就搬走了呀!聽說是回老家了,房子都賣了,搬家公司來了好幾輛車,東西都拉走了。」
「搬走了?回老家了?」我如遭雷擊,愣在原地,大腦一片空白。
怎麼會?為什麼不告訴我?樂樂不是在本地醫院治療嗎?為什麼要賣房子回老家?
無數個問號在我腦子裡盤旋,卻找不到一個合理的解釋。
回到家,我把事情告訴了趙鵬。他聽完,臉色鐵青,一言不發地坐在沙發上抽煙,一根接一根。煙霧繚繞中,我看不清他的表情,卻能感受到他身上散發出的冰冷怒氣。
「趙鵬,你說話啊……」我的聲音帶著哭腔。
他終於掐滅了煙頭,抬起頭,眼睛裡滿是紅血絲,聲音沙啞得可怕:「林舒文,我還能說什麼?我說的話,你聽過嗎?現在,你滿意了?」
那一刻,我所有的委屈、惶恐和不安,都化為了無地自容的羞愧。
我錯了,錯得離譜。
我賭上的是我們全家的積蓄,是我丈夫的信任,是我對二十年友情的全部認知。
而我,輸得一敗塗地。
第3章 消失的五年
何晴失聯後的日子,是我人生中最灰暗的一段時光。
那十八萬,像一塊巨大的石頭,沉甸甸地壓在我們夫妻倆的心上。我們不再談論換房子的事,那個話題成了一個禁忌,誰也不願觸碰。家裡的氣氛變得壓抑而沉悶,我和趙鵬之間的交流越來越少,常常是各自捧著手機,相對無言。
我知道他在生我的氣,氣我的自作主張,氣我的愚不可及。他沒有再大聲指責過我,但那種沉默的疏離,比任何激烈的爭吵都更讓我難受。
我開始瘋狂地尋找何晴。我去了她以前工作的單位,人事說她早就辭職了。我聯繫了所有我們共同的朋友,他們都表示很久沒有何晴的消息了。我甚至想過去報警,但警察問我:「有借條嗎?」
我搖了搖頭。
「有轉帳記錄嗎?」
「有。」

「那她當時借錢的理由是什麼?」
「她……她說孩子病了。」
「有證據證明她是在詐騙嗎?也許她真的有困難,只是暫時還不上。」
是啊,我沒有任何證據。我甚至無法向別人證明,何晴是「惡意」失聯,而不是「暫時」遇到了更大的困難。在所有人看來,這只是一筆沒有借條的民間借貸糾紛。除了自認倒霉,我別無他法。
時間久了,我也就認命了。
我把何晴所有的聯繫方式都拉黑了,我想用這種方式,把她從我的世界裡徹底清除出去。可每當夜深人靜,那個被背叛的場景,那些和趙鵬爭吵的畫面,就會像電影一樣在腦海里反覆上演。我一遍遍地問自己,為什麼?為什麼她要這麼對我?二十年的感情,難道就只值十八萬嗎?
為了填補那個巨大的財務窟窿,也為了麻痹自己,我開始拚命工作。我主動加班,承接最棘手的項目,像個不知疲倦的陀螺。趙鵬看在眼裡,默默地承擔了家裡所有的家務。他會在我加班晚歸時,給我留一盞燈,熱一碗湯。
有一天深夜,我做完一個項目方案,疲憊地回到家,發現他還沒睡,正坐在客廳等我。
他把一杯溫好的牛奶遞給我,輕聲說:「舒文,別這麼拼了,錢沒了可以再掙,身體垮了就什麼都沒了。」
我看著他眼裡的心疼,積壓了許久的委屈和愧疚瞬間決堤,我抱著他,嚎啕大哭。
他輕輕拍著我的背,嘆了口氣:「都過去了。就當是花錢買個教訓吧。以後,我們家裡的事,不管大小,都一起商量,好嗎?」
我用力地點了點頭。
那一晚,我們聊了很久。我們談起了那消失的十八萬,談起了我們被擱置的計劃,也談起了我們之間出現的裂痕。那場遲來的溝通,像一場春雨,洗去了蒙在我們心頭的塵埃。
石頭雖然還在,但我們決定一起扛。
生活漸漸回到了正軌。兩年後,靠著我們倆的努力,又重新攢下了一些錢。雖然還不夠換大房子,但我們在郊區買了一套小戶型,總算有了真正屬於自己的家。搬家那天,陽光很好,我和趙鵬站在陽台上,看著窗外,都笑了。
日子一天天過去,何晴這個名字,連同那段不堪的往事,似乎真的被我塵封了起來。我以為,這件事就會這樣,成為我人生中一個永遠無法解開的謎,一個永不癒合的傷疤。
我甚至已經做好了,這輩子再也見不到她,也再也要不回那筆錢的準備。
直到五年後的今天,這個電話,毫無徵兆地打了進來。
第4章 遲來的真相
「我是何晴。」
當這三個字從聽筒里傳來,我握著手機的手,不受控制地顫抖起來。
五年了,這個聲音,我曾在夢裡咒罵過無數次,也曾在某個瞬間,恍惚地以為自己聽見過。可當它真實地響起時,我除了震驚,竟然沒有預想中的憤怒和激動。
我的喉嚨像是被什麼東西堵住了,發不出任何聲音。
電話那頭,似乎也陷入了長久的沉默。我能聽到她急促而壓抑的呼吸聲,仿佛也用盡了全部的力氣。
「舒文……」她又輕輕地喚了一聲,聲音裡帶著濃重的鼻音和一絲怯意,「我知道,我沒臉給你打電話。我……我對不起你。」
「你在哪兒?」我終於找回了自己的聲音,乾澀而沙啞。
「我就在這座城市,我回來了。」她說,「舒文,我們能……見一面嗎?我想把一切都告訴你,還有……把錢還給你。」
把錢還給我?
我愣住了。我以為這筆錢早已打了水漂,從未想過有朝一日還能回來。
我的大腦飛速運轉著。她為什麼現在出現?這五年她去了哪裡?當年到底發生了什麼?一個又一個謎團,像瘋長的野草,瞬間占據了我的全部思緒。
「好。」我聽見自己說,「時間,地點。」
我們約在了一家離我家不遠的茶館,一個安靜的包間裡。
掛了電話,我坐在沙發上,久久無法平靜。趙鵬從廚房出來,看到我失魂落魄的樣子,關切地問:「怎麼了?誰的電話?」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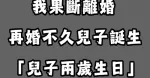
 武巧輝 • 3K次觀看
武巧輝 • 3K次觀看
 楓葉飛 • 2K次觀看
楓葉飛 • 2K次觀看









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