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醫生,我愛人怎麼樣了?」林先生沖在最前面,聲音都在發抖。
醫生看了看我們,嘆了口氣,說:「暫時脫離生命危險了。但是……」
我們所有人的心,都提到了嗓子眼。
「但是病人失血過多,加上腦部受到撞擊,陷入了深度昏迷。什麼時候能醒過來,不好說。也許幾天,也許幾個月,也許……」
醫生沒有把最後那句話說出來,但我們都懂了。
林先生的身體晃了晃,差點摔倒。我趕緊扶住他。
「家屬要做好長期護理的準備。」醫生說完,拍了拍林先生的肩膀,就轉身離開了。
江舒被從搶救室里推了出來,轉入了重症監護室。
隔著厚厚的玻璃,我看著她躺在病床上,身上插滿了各種管子,臉上沒有一絲血色,像一朵瞬間凋零的白玫瑰。
我的心,疼得無法呼吸。
林先生趴在玻璃窗上,無聲地流著淚。
我站在他身後,在心裡默默地發誓:江老師,你放心。只要我陳蘭還有一口氣,這個家,我就替你守著。
第7章 守著一個家
江舒在ICU里待了半個月,情況才算穩定下來,轉入了普通病房。
但這半個月,對林家來說,像是過了一個世紀那麼漫長。
林先生以肉眼可見的速度憔悴下去,頭髮白了一大半,整個人瘦得脫了形。他白天要去公司處理堆積如山的工作,晚上就來醫院守著,幾乎沒怎麼合過眼。

林安的情況也很糟糕。車禍的陰影,加上母親的病危,讓這個原本陽光開朗的少年變得沉默寡言,甚至出現了嚴重的心理問題。他把自己關在房間裡,不見任何人,不跟人說話,整夜整夜地做噩夢。
這個家,在瞬間,就塌了半邊天。
而我,成了支撐這個家不倒下的另一根柱子。
我沒有再提回老家的事。我給兒子打了個電話,告訴他這邊出了急事,我暫時走不了。張強雖然有些不高興,抱怨我耽誤了他結婚,但聽說是人命關天的大事,也沒再多說什麼。
我把那十萬塊錢現金,連同林先生給我的那張銀行卡,都交給了林先生。
「林先生,現在是用錢的時候,這些你先拿著。密碼是小安的生日。」
林先生看著我,眼圈紅了,他沒有推辭,只是啞著嗓子說了一句:「蘭姐,大恩不言謝。」
我重新回到了那個熟悉的廚房,重新繫上了那條洗得發白的圍裙。
我每天變著花樣地給林先生和林安做有營養的飯菜,然後用保溫桶裝好,一份送到公司,一份送到醫院,一份放在林安的房門口。
林先生總是沒什麼胃口,我就逼著他吃。我說:「你要是倒了,江老師醒了看見你這樣,心裡該多難受。」
林安不肯開門,我就把飯菜放在門口,過一個小時再去收。有時候飯菜原封不動,有時候會少一些。我知道,他心裡有道坎,需要時間慢慢過去。
除了做飯,我還要打理整個家。洗衣,打掃,採購……我把自己變成一個高速旋轉的陀螺,不敢停下來。我怕一停下來,就會被巨大的悲傷和無力感吞噬。
江舒轉到普通病房後,林先生請了兩個專業的護工,24小時輪流看護。但我還是不放心,每天都要親自去醫院,幫她擦洗身體,跟她說話。
我坐在她的病床前,拉著她冰涼的手,絮絮叨叨地跟她講家裡的事。
「江老師,你快點醒過來吧。家裡的蘭花又開花了,白色的,可好看了。」
「小安這孩子,最近懂事多了。我放在他門口的飯,他都吃了。他還問我,你什麼時候能回家。」
「林先生瘦了好多,你再不醒,他都要變成老頭子了。你醒了可得好好說說他。」
我不知道她能不能聽見,但我相信,只要我一直說,一直呼喚她,她就一定能感受到。
日子就在這種忙碌又壓抑的等待中,一天天過去。
轉眼,秋天來了。
林安在心理醫生的幫助下,情況漸漸好轉。他開始走出房門,雖然話還是不多,但至少願意跟我交流了。
有一天,我正在廚房燉湯,他走進來,默默地站在我身後。
「陳姨。」他忽然開口。
「哎。」我應了一聲,回過頭。
「對不起。」他說,「還有,謝謝你。」
少年人的道歉和感謝,簡單又笨拙,卻讓我瞬間紅了眼眶。
我轉過身,摸了摸他的頭:「傻孩子,跟姨說這些幹什麼。快去寫作業吧,湯馬上好了。」
他點了點頭,轉身離開。看著他不再佝僂的背影,我心裡的一塊大石頭,總算落了地。
只要孩子好好的,這個家,就還有希望。
冬至那天,上海下了一場罕見的雪。
我包了餃子,是江舒最愛吃的薺菜豬肉餡。我帶著餃子和保溫桶里的湯,去了醫院。
病房裡很安靜,只有儀器發出的滴滴聲。
我像往常一樣,坐在江舒的床邊,一邊給她按摩手臂,防止肌肉萎縮,一邊跟她說話。
「江老師,下雪了,今年的第一場雪。你以前不是總念叨著,想看一場大雪嗎?等你好了,我陪你和小安去堆雪人。」
我說著說著,眼淚就掉了下來。
已經快半年了,她還是沒有任何要醒過來的跡象。醫生說,時間拖得越久,希望就越渺茫。
我有時候也會絕望,也會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偷偷地哭。可是一到白天,我就得重新打起精神,因為這個家需要我。
就在我擦眼淚的時候,我忽然感覺到,我握著的那隻手,手指……似乎動了一下。
那一下,非常輕微,輕微到我以為是自己的錯覺。
我立刻屏住了呼吸,死死地盯著她的手。
我的心跳得像擂鼓一樣。
「江老師?」我試探著,輕輕地叫了一聲。
幾秒鐘後,那隻我握了無數次的手,又一次,輕輕地,回握了我一下。
雖然無力,但我清晰地感受到了!
「醫生!醫生!」我激動地衝出病房,用盡全身力氣大喊起來。
醫生和護士很快趕了過來,給江舒做了一系列檢查。
林先生和林安也接到了我的電話,瘋了一樣地趕到醫院。
我們所有人都圍在病床前,緊張地看著醫生。
半個小時後,醫生摘下聽診器,臉上露出了久違的笑容。
「奇蹟,真是奇蹟。」他說,「病人的腦電波活動明顯增強,各項生命體徵都在好轉。家屬要多跟她說話,多刺激她,她有很強的求生意識,很有可能……很快就能醒過來了。」
我們所有人都喜極而泣。
林先生抱著林安,父子倆哭成一團。我站在一邊,捂著嘴,眼淚止不住地往下流。
我知道,這個家,終於要守得雲開見月明了。
尾聲
一年後。
我老家縣城,「幸福里」小區。
午後的陽光,透過乾淨的玻璃窗,灑在我那套八十九平米的新家裡。
我坐在陽台的搖椅上,看著客廳里,張強和小慧正在逗他們剛滿月的兒子。小傢伙咿咿呀呀的,可愛極了。
我的生活,在過去的一年裡,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。
江舒在那個冬日之後,半個月就甦醒了。雖然身體還很虛弱,需要漫長的康復,但她終究是回來了。
她醒來後,拉著我的手,說的第一句話是:「蘭姐,讓你受苦了。」
我哭著說:「不苦,只要你好好的,就不苦。」
我在上海又待了半年,直到江舒的身體基本康復,能下地走路,我才在他們的再三催促下,回了老家,準備兒子的婚事。
林先生把我送我的那套房子的鑰匙,親手交給了我。他說:「蘭姐,這是你的家。但上海那個家,也永遠是你的家。隨時回來。」
我兒子張強,在經歷了這一切之後,也像是長大了。他不再抱怨,不再覺得我傻。他鄭重地跟我道了歉,說他明白了,人與人之間,有些情義,是不能用錢來衡量的。
婚禮辦得很熱鬧。林先生一家,也專程從上海趕了過來。
林安長得更高了,也更穩重了。他抱著我的孫子,愛不釋手,一個勁兒地叫「小弟弟」。
江舒的氣色很好,雖然走路還有些慢,但那份知性的氣質,一點沒變。她給我包了一個大大的紅包,說是給孩子的見面禮。
我們兩家人,像真正的親人一樣,坐在一起,吃了一頓團圓飯。
飯桌上,林先生舉起酒杯,對我說:「蘭姐,我們敬你一杯。沒有你,就沒有我們這個家的今天。」
我端起杯子,眼眶濕潤。
我知道,我這輩子,值了。
如今,我每天的生活,就是含飴弄孫,養花種草。偶爾,我會和江舒視頻通話,聊聊家常。她說她現在已經學會燉排骨湯了,雖然味道,還是比不上我做的。
林安考上了上海一所頂尖的大學,他說,等放假了,要來我這裡住幾天,嘗嘗我做的菜。
我常常會想起那個改變了我一生的牛皮紙袋。
它讓我明白,人生的回報,並非總是以金錢的形式出現。有時候,它是一份沉甸甸的尊重,一份將心比心的善意,一份超越血緣的親情。
這十二年的保姆生涯,我付出了青春和汗水,卻收穫了一個家的溫暖,一份後半生的安穩,和一顆被真情填滿的、富足的心。
陽光正好,微風不燥。我看著懷裡熟睡的小孫子,心裡一片寧靜。

我知道,我的故事,不是一個保姆的逆襲,而是一個關於人心換人心的,最樸素的證明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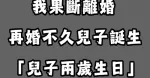
 武巧輝 • 3K次觀看
武巧輝 • 3K次觀看
 楓葉飛 • 2K次觀看
楓葉飛 • 2K次觀看









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