當12年保姆,辭職時主家給我一紙袋,本以為是現金,打開後傻眼了
那個牛皮紙袋裡,沒有我以為的厚厚一沓現金。
只有一本嶄新的房產證,和一張薄薄的銀行卡。
房產證上,戶主的名字,是我的。
整整十二年,四千三百多個日夜,我把一個嗷嗷待哺的嬰兒帶成了一個挺拔的少年,把一個清冷的大房子捂成了一個有煙火氣的窩。我以為,這十二年的情分,最終會以一種最俗氣也最直接的方式了結,就像所有主顧和保姆之間心照不宣的規則那樣。
可思緒,還得拉回到我提出辭職的那個下午。
第1章 一碗蓮子湯
上海的六月,黃梅天,空氣黏稠得像化不開的糖稀。我關掉抽油煙機,廚房裡那股子悶熱才算找到了宣洩的出口,爭先恐後地從沒關嚴實的窗戶縫裡擠出去。
鍋里溫著蓮子百合湯,是給小安準備的。林安,我的小僱主,今年高二,學業緊,人也跟著抽條,瘦得像根豆芽菜。他媽媽江舒是大學教授,講究科學飲食,夏天從不讓他碰冰的,只信我燉的這些清心安神的湯湯水水。
我擦了擦手,解下洗得發白的圍裙,疊得方方正正放在檯面上。然後,我深吸了一口這熟悉的、混雜著飯菜香和淡淡油煙味的空氣,走向客廳。
江舒正坐在沙發上看稿子,戴著一副無框眼鏡,顯得文靜又疏離。她聽見我走過來的腳步聲,頭也沒抬,只是習慣性地問:「蘭姐,湯好了?」
「好了,溫在鍋里呢,等小安回來喝正好。」我站定在她面前,兩隻手有些不安地在身前交握著,指甲掐著手心,傳來一陣細微的痛感。
這番對話,十二年來,我們重複了不下幾千遍。可今天,我卻要在後面加上一句完全不同的話。
「江老師,」我清了清嗓子,聲音有點發乾,「有件事,我想跟您商量一下。」
江舒終於從稿子裡抬起了頭,扶了扶眼鏡,目光落在我臉上。她的眼神很清亮,像一汪深潭,總讓人覺得看不透。她似乎察覺到了我的侷促,放下手裡的稿子,身體微微前傾:「蘭姐,你說,什麼事?」
「我……」我張了張嘴,準備好的說辭到了嘴邊,又覺得沉甸甸的,「我家裡有點事,我兒子……他要結婚了,我得回去給他操持操持。所以,我想……我想辭了這份工。」
我說得很慢,幾乎是一字一頓。每說出一個字,心裡就像被抽走了一分力氣。
客廳里一瞬間安靜下來,只剩下中央空調細微的送風聲。
江舒臉上的表情凝固了。她沒有立刻說話,只是靜靜地看著我,那雙清亮的眼睛裡,慢慢浮現出一種我從未見過的複雜情緒,有驚訝,有不解,甚至還有一絲……慌亂?
「辭職?」她重複了一遍,聲音很輕,像怕驚擾了什麼,「怎麼這麼突然?是你兒子那邊催得急嗎?還是……是我們有哪裡做得不好,讓你不舒心了?」
我趕緊擺手,急急地解釋:「沒有沒有,江老師,您和林先生待我沒得說,比我娘家人還親。是我自己的事,孩子大了,當媽的總得盡到責任。他那邊定在十月份辦酒,我總得提前回去準備,家裡老房子要翻修,還得見見親家,事兒多。」
這些都是實話。我老家的兒子張強,談了個對象,總算要成家了。我這個當媽的,心裡高興,也確實該回去盡一份心力。我出來做保姆,一是為了給丈夫治病,後來丈夫走了,就是為了給兒子攢錢娶媳婦。如今,目標算是達成了。
江舒沉默了。她低下頭,手指無意識地摩挲著沙發的扶手,那上面有上好的絲絨,被她捻過來、捻過去。
「十二年了啊……」她忽然感慨了一句,聲音裡帶著一絲不易察覺的悵然,「我都快忘了,沒有你的日子,這個家會是什麼樣。小安……小安怎麼辦?」
提到林安,我的心猛地一揪。
十二年前我剛來這個家的時候,林安才剛滿一歲,話都說不利索,整天跟在我屁股後面「姨姨、姨姨」地叫。他爸林偉是建築設計師,常年出差,忙得腳不沾地。江舒那時候剛評上副教授,課業和研究項目壓得她喘不過氣。可以說,林安是我一手一腳帶大的。
他第一次發燒,是我抱著他在醫院排了一夜的隊。他第一次學走路,是扶著我的腿。他第一次開口叫的不是「爸爸媽媽」,而是含糊不清的「姨」。
他是我看著長大的孩子,雖然沒有血緣,但那份感情,比什麼都真。
「小安也大了,懂事了。」我強忍著心裡的酸澀,儘量讓自己的聲音聽起來平穩,「他現在學習緊張,您和林先生多費點心,請個鐘點工做做飯、搞搞衛生,應該也還好。」
江"還好"兩個字說出口,我自己都覺得沒什麼底氣。這個家,早就習慣了我的存在。林先生的胃不好,只能吃軟爛的東西;江舒有輕微的潔癖,毛巾必須每天用開水燙過;林安對芒果過敏,但他又饞,我總得變著法子給他做沒有芒果卻有芒果味的甜品。這些瑣碎的、不成文的規矩,刻在這個家的骨子裡,也刻在我的腦子裡。換一個人來,怎麼可能「還好」?
江舒嘆了口氣,靠回沙發里,顯得有些疲憊。「蘭姐,我知道,你也有自己的家,自己的孩子。我沒道理攔著你。只是……你讓我想想,這事太突然了,我得和老林商量一下,也得……也得找個機會跟小安說。」
她的通情達理,反倒讓我心裡更不是滋味。我多希望她能像別的僱主一樣,要麼不高興地抱怨幾句,要麼乾脆利落地談錢。可她沒有,她只是難過,只是在為這個家沒有我的未來而發愁。
「不急的,江老師,」我輕聲說,「我還能再做兩個月,做到八月底,等小安放了暑假,您再慢慢找人。總得有個交接。」
「嗯。」江舒點了點頭,重新拿起那份稿子,卻一個字也看不進去了。她對著空氣發了會兒呆,然後說:「蘭姐,你去忙吧。晚飯……簡單點就行。」
我應了一聲,轉身走回廚房。
一門之隔,我靠在冰冷的琉璃檯面上,心裡空落落的。我一直以為,辭職會是一種解脫,是我完成了任務,可以光榮退場了。可真到了這一天,我才發現,十二年的光陰,早已把我和這個沒有血緣關係的家庭,牢牢地捆綁在了一起。
這種捆綁,不是靠合同,也不是靠工資,而是靠一碗碗熱湯,一件件乾淨的衣服,一次次深夜的陪伴,慢慢織成的,剪不斷,理還亂。
晚上七點,林安背著沉甸甸的書包回來了。他一進門,就把書包甩在玄關,有氣無力地喊:「陳姨,我餓死了,有什麼好吃的?」
我端著最後一盤菜從廚房出來,笑著說:「就知道你餓了。洗手吃飯,今天有你最愛吃的糖醋排骨。」
林安歡呼一聲,跑到我身邊,像小時候一樣,腦袋湊過來,在我剛出鍋的菜上深深吸了一口氣:「哇,真香!陳姨你就是我的神!」
他已經比我高出一個頭了,肩膀也寬了,是個大小伙子了。可是在我面前,他永遠是那個流著鼻涕撒嬌要糖吃的小屁孩。
飯桌上,氣氛有些沉悶。
林先生今晚難得沒有應酬,在家吃飯。他話不多,吃飯的時候更是沉默。江舒也沒什麼胃口,只是一個勁兒地給林安夾菜。
我照例沒有上桌,這是我給自己定的規矩。我端著一碗飯,坐在廚房門口的小凳子上,一邊吃,一邊聽著餐廳里的動靜。
「小安,多吃點蔬菜。」江舒說。
「知道了媽,你都說了八百遍了。」林安的聲音裡帶著少年人特有的不耐煩。
「你陳姨辛辛苦苦做的,別浪費。」林先生開口了,聲音低沉。
林安扒拉著碗里的飯,嘟囔道:「我哪有浪費……」
我聽著這些對話,心裡五味雜陳。這些煙火氣,這些瑣碎的日常,從今往後,就要離我遠去了。
飯後,我收拾完廚房,準備回自己的房間。路過客廳時,聽見江舒和林先生在低聲說話。
「……跟她談了嗎?」是林先生的聲音。
「談了。她兒子要結婚,要回去。鐵了心要走。」江舒的聲音里滿是無奈。
「唉,也是。總不能耽誤人家一輩子。」林先生嘆了口氣,「那錢準備好了嗎?按我們之前說的,這些年她不容易,得多給點。不能虧待了她。」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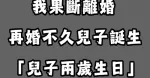
 武巧輝 • 3K次觀看
武巧輝 • 3K次觀看
 楓葉飛 • 2K次觀看
楓葉飛 • 2K次觀看









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