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媽把拆遷房給我弟,卻讓我給她買房還要寫她名,以後留給她兒孫
媽,那套房子,我不買。
當著所有親戚的面,我清清楚楚地說出了這句話,聲音不大,卻像一顆石子投進了滾沸的油鍋。
我媽趙桂蘭那張原本還在高談闊論、描繪著未來美好藍圖的臉,瞬間凝固了。她眼裡的光彩一寸寸熄滅,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全然的、不可置信的錯愕。
從我大學畢業工作那天起,整整十五年,我像一頭被設定好程序的黃牛,勤勤懇懇地朝家裡輸送著我的血汗。工資的三分之一雷打不動地打回家裡,年節的紅包永遠最厚,弟弟林濤的學費、生活費,甚至他第一輛二手車的首付,都有我的一份。我媽常說:「靜靜最懂事,以後肯定有大出息,是家裡的頂樑柱。」我曾以為,這是誇獎,是愛。
直到那天,我才恍然大悟,原來在她的世界裡,「頂樑柱」的意思,就是用來犧牲和支撐的,而不是被疼愛的。
可這一切清醒,都來得太晚了。故事,要從那個燥熱的、充滿了鐵鏽和塵土味道的夏天說起,從我媽打來的那個電話開始。
第1章 老房子的最後一口氣
「靜靜啊,你爸那套老房子,終於要拆了。」
電話那頭,我媽趙桂蘭的聲音帶著一種壓抑不住的興奮,像是守著一鍋陳年老湯,終於等到了揭蓋聞香的時刻。
我正陷在辦公椅里,核對著一份冗長的財務報表,密密麻麻的數字看得我眼暈。窗外,是城市鋼筋水泥的森林,三十層的高度,讓人感覺自己像個懸浮在半空的孤島。我捏了捏眉心,把聽筒換到另一邊耳朵,「是嗎?那挺好的,定下來了?」
「定了定了,文件都下來了!按人頭加面積,能分一套大的,一百二十平,三室兩廳!位置也好,就在咱們區新建的那個『錦繡家園』,離地鐵口近著呢!」
我能想像到我媽在電話那頭眉飛色舞的樣子。老房子是父親單位分的,一棟上世紀八十年代的紅磚筒子樓,六十平米不到,陰暗潮濕,承載了我整個童年和少年時代的記憶。那裡有夏夜裡嗡嗡作響的吊扇,有樓道里鄰居家飄來的飯菜香,也有我和弟弟林濤為了一根冰棍打得不可開交的吵鬧聲。
父親去世得早,是我媽一個人拉扯我們姐弟倆長大。記憶里,她的背影總是緊繃的,像一張隨時會斷裂的弓。她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我們身上,尤其是對小我三歲的弟弟林濤。
「那太好了,媽。這下你跟林濤住著也寬敞,不用擠在那個小兩室里了。」我由衷地為她高興。這些年,她守著那套老房子,最大的念想就是這個。
電話那頭沉默了一下,我媽清了清嗓子,語氣忽然變得有些鄭重,「靜靜,你這個周末……有空回家一趟嗎?帶上小方(我丈夫方毅)一起。關於這個房子的事,我跟你和林濤,得好好商量一下。」
我心裡「咯噔」一下。
我媽的「商量」,從來都不是真正的商量。它通常是一個通知,包裹著「為了你好」或者「一家人不說兩家話」的糖衣,讓你無法拒絕。一種不祥的預感,像潮濕天氣里牆角蔓延的霉斑,悄無聲息地在我心底擴散開來。
「好,我看看周末有沒有加班,儘量回去。」我沒有立刻答應,給自己留了一點餘地。
掛了電話,辦公室的中央空調依舊吹著冷風,我卻覺得有些胸悶。我看著電腦螢幕上反射出的自己,三十七歲,眼角已經有了細微的紋路,一身得體的職業裝,看起來是個標準的都市白領。可只有我自己知道,這身光鮮的外殼下,包裹著一顆多麼疲憊和被拉扯的心。
方毅下班回來,看到我坐在沙發上發獃,便走過來挨著我坐下。「怎麼了?今天開會又被老闆批了?」他笑著揉了揉我的頭髮。
我把頭靠在他的肩膀上,把媽的電話內容說了一遍。
方毅聽完,沉默了片刻,然後緩緩開口:「的意思,我猜,是想把拆遷房直接給林濤。」
我心裡一緊,其實我也想到了,只是不願意承認。「怎麼會?房本上是我爸的名字,我和林濤都有份的。再說了,媽一個人住,林濤也還沒結婚,給他那麼大的房子幹嘛?」
「靜氣,」方毅總是叫我「靜氣」,說我性格太靜,容易受氣,「你別忘了,林濤談了快一年的女朋友,差不多該到談婚論嫁的時候了。這套拆遷房,就是現成的婚房。這是在為她兒子鋪路呢。」
方毅的話像一根針,精準地刺破了我用來自我安慰的那個氣泡。
是啊,林濤。我那個被我媽從小寵到大的弟弟。小時候,家裡但凡有點好吃的,我媽總是先緊著他;我穿的衣服是親戚家孩子穿舊的,而林濤永遠有新衣服;我考了全班第一,我媽只是點點頭說「別驕傲」,而林濤在學校運動會拿了個紀念獎,她能高興得請街坊鄰居吃糖。
我媽總說:「你是姐姐,要讓著弟弟。」
這句話,像一道緊箍咒,伴隨了我整個成長過程。我讓出了零食,讓出了新衣服,讓出了被偏愛的權利。工作後,我更是理所當然地承擔起了「幫扶」弟弟的責任。我媽說:「林濤剛畢業,工資低,你這個當姐的,多幫襯著點。」於是,我每個月給他轉生活費。我媽又說:「林濤要談朋友,沒輛車出門沒面子,你幫他湊點。」於是,我拿出了自己準備買車的積蓄。
方毅對此頗有微詞,但他了解我的性格,也心疼我媽守寡不易,多數時候只是勸我量力而行,別委屈了自己。
可這一次,是房子。是我們父親留下的,唯一值錢的東西。
「不可能,」我搖著頭,像是在說服自己,「媽不會這麼偏心的。這房子裡,也有我的一份。她最多是讓林濤先住著,產權上肯定不會亂來。」
方毅嘆了口氣,握住我冰涼的手:「希望如此吧。不過,你得有個心理準備。周末回去,不管說什麼,先別急著答應。就說要回來跟我商量。記住了嗎?」
我點了點頭,心裡卻亂成一團麻。那個承載了我所有童年記憶的老房子,在它即將消失的時候,似乎也要帶走我們這個家最後一點溫情和體面。
那個周末,天氣悶熱得像個蒸籠。我和方毅提著大包小包的營養品和水果,回到了那棟熟悉的紅磚樓。樓道里堆滿了雜物,牆壁上用紅漆噴著大大的「拆」字,像一道道刺目的傷疤。
推開家門,我媽和林濤正坐在客廳里看電視。看見我們,我媽立刻笑開了花,熱情地接過東西,「哎呀,回來就回來,還買這麼多東西幹嘛,凈花錢!」
林濤也站起來,沖我笑了笑,喊了聲:「姐,姐夫。」他二十出頭,長得高高瘦瘦,眉眼間有幾分父親的影子,但眼神里卻少了幾分擔當,多了些被慣出來的安逸。
飯桌上,我媽做了一大桌子菜,不斷地往方毅和林濤碗里夾。她對方毅這個女婿一向很滿意,工作體面,對我又好。
「小方啊,多吃點,看你最近都瘦了。」
「林濤,這個紅燒肉是你最愛吃的,媽燉了好幾個小時呢。」
她熱情地照顧著每一個人,除了我。仿佛我只是一個陪客。我習慣了,默默地低頭吃飯。
酒過三巡,菜過五味,我媽終於放下了筷子,清了清嗓子,進入了正題。
「今天叫你們回來,就是為了房子的事。」她看了一眼我,又看了一眼林濤,最後目光落在林濤身上,充滿了慈愛和期許,「我和你弟弟商量過了。這套拆遷房,一百二十平,就直接寫林濤的名字。」
儘管方毅已經給我打了預防針,但當這句話從我媽嘴裡說出來時,我的心還是猛地沉了下去。像被人迎頭澆了一盆冰水,從頭涼到腳。
我握著筷子的手,不自覺地收緊了。
第2章 「你是姐姐,就該幫弟弟」
飯桌上的空氣,在那一瞬間仿佛凝固了。
林濤埋著頭,假裝專心致志地對付碗里最後一塊紅燒肉,耳朵尖卻微微泛紅。方毅的臉色沉了下來,他放下筷子,卻沒有作聲,只是用眼角的餘光看著我,把發言權留給了我。
我深吸一口氣,努力讓自己的聲音聽起來平靜一些:「媽,為什麼?這房子是爸留下的,我們姐弟倆都有份。直接寫林濤一個人的名字,不合適吧?」
我媽似乎早就料到我會這麼問,臉上沒有絲毫意外。她慢條斯理地拿起桌上的茶杯,呷了一口,才不緊不慢地說道:「有什麼不合適的?你是嫁出去的女兒,潑出去的水。林濤是兒子,是咱們老林家唯一的根,這房子不給他給誰?他馬上就要結婚了,總得有套婚房吧?難道讓他女朋友跟著他住宿舍嗎?」
這一連串的反問,理直氣壯,帶著一種不容置疑的威嚴。在她眼裡,這一切似乎都是天經地義,是刻在骨子裡的老規矩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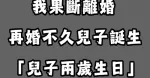
 武巧輝 • 3K次觀看
武巧輝 • 3K次觀看
 楓葉飛 • 2K次觀看
楓葉飛 • 2K次觀看









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