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9歲繼母慫恿父親送我走,我年入32萬為養父買房,她跪求我
二十年後,在我為養父買的新房客廳里,那個當年親手把我送走的繼母,陳玉芬,直挺挺地跪在了我面前。
她的眼淚和哀求,像一場遲到了二十年的暴雨。
這二十年里,我從一個被嫌棄的九歲女孩,長成了年薪三十二萬的城市白領。我學會了咽下所有委屈,學會了依靠自己,更學會了如何去愛那個給了我一個家的男人——我的養父,張援朝。
可記憶的閥門一旦打開,那股夾雜著樟腦丸和冷漠氣味的童年,還是瞬間將我淹沒,回到了那個悶熱的夏日午後。
第1章 被拋棄的夏天
九歲那年的夏天,空氣是粘稠的,知了聲嘶力竭地叫著,仿佛要把整個世界都給掀翻。
我叫林曉晚,這個名字是我媽給起的,她說希望我的生活,即使有黑夜,也總能迎來拂曉。可在我五歲那年,她生病走了,我的拂曉也跟著一起消失了。
父親林建國很快再婚,娶了在紡織廠當會計的陳玉芬。她帶來了自己的兒子,比我小一歲的林浩。從那天起,我們家那間不大的兩居室里,我成了多出來的那一個。
陳玉芬是個很會「做人」的女人,至少在外人看來是這樣。她從不大聲呵斥我,甚至會夾菜給我,但那雙眼睛裡的疏離和算計,像淬了冰的針,總能精準地扎在我最敏感的地方。
家裡只有一個小電風扇,永遠對著林浩吹。飯桌上最後一塊紅燒肉,永遠會「不小心」滑進林浩的碗里。而我的父親林建國,他總是裝作看不見,或者用一句「浩浩還小,你是姐姐,讓著他點」來結束所有潛在的爭執。
我漸漸學會了沉默,像一隻壁虎,努力把自己融進牆壁的顏色里,不發出任何聲音,不占用多餘的空間。
那個夏天,矛盾終於在一個悶熱的午後爆發了。
那天林浩非要搶我媽留下的唯一一個鐵皮文具盒,那是我最寶貴的東西,上面畫著一隻現在看起來很土氣的小兔子。我不肯給,他就在地上撒潑打滾,哭得驚天動地。
陳玉芬聞聲從廚房衝出來,一把奪過我手裡的文具盒,塞到林浩懷裡,嘴裡哄著:「浩浩不哭,媽媽給你,這就是你的。」
我瘋了一樣撲上去想搶回來,卻被她一把推倒在地。我的膝蓋磕在水泥地上,火辣辣地疼,血一下子就滲了出來。
我沒哭,只是死死地盯著她。
那一刻,我從她眼中看到了毫不掩飾的厭惡。
晚上,父親下班回來。我以為他會為我主持公道,至少會問問我的傷。可他只是聽陳玉芬添油加醋地講完「我的不懂事」,然後疲憊地嘆了口氣。
那天晚上,我躲在自己那張用木板搭的小床後面,聽見了他們臥室里的爭吵。聲音很壓抑,但字字句句都像錐子,扎進我的耳朵里。
「建國,這日子沒法過了!你看看曉晚那眼神,跟狼崽子似的,我看著都瘮得慌。家裡就這麼大點地方,浩浩都快沒地方下腳了。」這是陳玉芬的聲音,尖銳又委屈。
「那能怎麼辦?她是我女兒。」父親的聲音聽起來很無力。
「女兒?你當她是女兒,她當浩浩是弟弟嗎?遲早要出事!我跟你說,我表姐夫他們村裡,有個叫張援朝的,老光棍一個,人老實,就是沒個一兒半女的。前兩天還託人問,想領個孩子作伴。曉晚送過去,不比在咱們這兒受氣強?人家肯定當親生的疼。」
「這……這怎麼行?傳出去我林建國的臉往哪兒擱?」
「有什麼不行的?就說是送去鄉下親戚家住幾年,對身體好。等過幾年大了,懂事了,再接回來不就行了?建國,你得為浩浩想想,為我們這個家想想啊!有她在,這個家永遠安生不了!」
之後是長久的沉默。
我蜷縮在黑暗裡,渾身發抖。我期待著父親能怒吼,能拍桌子,能衝出來把我抱在懷裡,告訴陳玉芬,這是他的女兒,誰也別想送走。
可是沒有。
最後,我只聽到父親一聲長長的,仿佛耗盡了所有力氣的嘆息:「……唉,那就……先去看看吧。」
那個瞬間,我心裡的某個東西,碎了。
一個星期後,父親請了半天假,騎著那輛除了鈴鐺不響哪兒都響的二八大槓自行車,載著我去了陳玉芬口中那個「鄉下」。
一路上,他一句話都沒說。我坐在后座,緊緊攥著自己的小布包,裡面裝著那個被搶走又被父親偷偷塞還給我的鐵皮文具盒,還有幾件舊衣服。我不敢抱住他的腰,我們之間隔著一個拳頭的距離,那是我無法跨越的鴻溝。
車子停在一個破舊的泥瓦房前。一個皮膚黝黑、身材幹瘦的中年男人迎了出來,他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藍色工字背心,眼神看起來有些侷促,但很善良。
他就是張援朝。
父親和他簡單說了幾句,大概就是「孩子拜託你了」之類的話。然後他轉過身,從口袋裡掏出幾張被汗浸得有些潮濕的零錢,塞到我手裡。
「曉晚,聽張叔叔的話,爸爸……過陣子就來接你。」
他的眼神躲閃,不敢看我。
我看著他,這個我叫了九年「爸爸」的男人,沒有哭,也沒有鬧,只是用一種他看不懂的平靜眼神看著他。
然後,我把手裡的錢,又塞回了他的手裡。
我什麼都沒說,轉身走進了那個陌生的,即將成為我「家」的院子。
我沒有回頭看。我知道,從這一刻起,我和那個家,再也沒有關係了。那個夏天,我被我的親生父親,像一件多餘的舊家具一樣,送走了。
第2章 瓦房裡的燈光
張援朝的家,和我以前在城裡的家完全是兩個世界。
土坯牆,茅草頂,屋裡只有一張木板床,一張缺了角的八仙桌和兩條長凳。唯一的電器,是那根從房樑上垂下來的電燈泡,拉一下開關,昏黃的光芒就慢悠悠地灑滿整個屋子。
空氣里瀰漫著一股淡淡的煙火和泥土混合的氣味,不難聞,反而讓我有些莫名的心安。
張援朝似乎不怎麼會和孩子打交道。他把我領進屋,搓著手,顯得比我還緊張。
「那個……閨女,你就睡這張床,我……我晚上在旁邊搭個地鋪就行。」他指著那張唯一的床,磕磕巴巴地說。
我點點頭,沒說話。
他看我一直不吭聲,以為我害怕,又從一個破舊的木箱子裡翻了半天,翻出幾顆用玻璃紙包著的水果糖,小心翼翼地遞到我面前:「吃糖,甜。」
糖紙都有些發粘了,顯然是放了很久。我接過來,剝開一顆放進嘴裡,一股廉價的香精味瞬間在口腔里瀰漫開。
很甜,甜得有點發苦。
我對他說了來到這個家的第一句話:「謝謝叔叔。」
他好像鬆了一大口氣,咧開嘴笑了,露出兩排被煙燻得發黃的牙齒:「哎,哎!不客氣,以後這就是你家。」
「以後這就是你家。」

這句話,我在林建國和陳玉芬的家裡,從未聽過。
剛開始的日子是沉默的。我像一隻受了驚的小獸,對周遭的一切都保持著警惕。張援朝似乎看出了我的不安,他從不主動問我過去的事,只是默默地用行動表達著他的善意。
他會天不亮就起床,給我做一碗熱騰騰的雞蛋羹,上面小心翼翼地滴上幾滴香油。要知道,在這個年代的農村,雞蛋是精貴東西,是用來換鹽換油的。
他會把家裡唯一一把還算完好的小椅子搬到院子裡的樹蔭下,讓我坐在那裡看書寫字,而他自己則蹲在灶房門口,一邊編著竹筐,一邊時不時地抬頭看我一眼,眼神里是那種我從未見過的,小心翼翼的關懷。
他話不多,我們之間最常發生的對話是:
「閨女,餓不餓?」
「不餓。」
「閨女,冷不冷?」
「不冷。」
「閨女,作業寫完了嗎?」
「寫完了。」
直到有一天,我發了高燒。
那天半夜,我渾身滾燙,燒得迷迷糊糊,嘴裡不停地喊著「媽媽」。我感覺自己像掉進了一個冰火兩重天的深淵,一會兒冷得發抖,一會兒又熱得像要被烤乾。
是張援朝發現了我不對勁。他用他那粗糙得像砂紙一樣的手掌摸了摸我的額頭,驚得「哎呀」一聲。
那個夜晚,我一輩子都忘不了。
他把我用家裡唯一一床厚被子裹得嚴嚴實實,然後背起我,就衝進了漆黑的雨夜裡。鄉下的路坑坑窪窪,泥濘不堪,他深一腳淺一腳地跑著,嘴裡不停地念叨著:「閨女別怕,爸在,爸在……馬上就到衛生所了……」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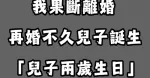
 武巧輝 • 3K次觀看
武巧輝 • 3K次觀看
 楓葉飛 • 2K次觀看
楓葉飛 • 2K次觀看









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