月子裡,丈夫說:孩子誰生的誰帶。我轉身把孩子落戶在了我娘家
我抱著剛滿月的女兒安安,在派出所戶籍大廳的等候區坐下時,心裡出奇的平靜。
工作人員喊到我名字的那一刻,我甚至還能對他笑一笑。
戶口本上,「戶主」一欄,端端正正地印上了我父親林建軍的名字。我的女兒,林安安,成了我娘家戶口本上新的一員。
從那天起,整整三年,我丈夫張偉看我的眼神里都帶著一絲說不清的忌憚。他再也沒敢說過那句「孩子誰生的誰帶」,也沒再把家務和育兒當成我一個人的理所當然。這三年,我們吵過,鬧過,冷戰過,最終也慢慢學著如何真正地成為一對父母,而不是一個「母親」和一個「甩手掌柜」。
但這一切的起點,都要回到那個悶熱的、連空氣都帶著奶腥味的夏天,回到我還在坐月子的那間朝北的小臥室里。
第1章 月子裡的那句話
六月的風是熱的,黏膩地糊在皮膚上,怎麼也吹不幹。
我坐月子的那間臥室,窗簾拉得嚴嚴實實,一絲風也透不進來。婆婆陳桂芳信奉老理兒,說月子裡不能見風,不能開窗,不然老了要得頭風病。於是,這間十來平米的小屋,就成了一個密不透風的蒸籠,混雜著汗味、中藥味,還有嬰兒身上淡淡的奶腥氣。
我叫林舒雅,今年二十八歲,剛剛經歷了一場耗盡我半條命的生產。女兒安安睡在我身邊,小臉皺巴巴的,像個紅皮小猴子,可在我眼裡,卻是天底下最珍貴的寶貝。剖腹產的傷口還在隱隱作痛,每一次翻身、起床,都像是有無數根針在扎。身體的虛弱和激素的斷崖式下跌,讓我的情緒像一根繃得極緊的弦,隨時都可能斷裂。
而我的丈夫張偉,此刻正坐在客廳的電腦前,耳機里傳來激烈的遊戲廝殺聲,間或夾雜著他興奮的喊叫:「推塔!推塔!漂亮!」
這聲音像一把鈍刀子,一下一下地割著我的神經。
安安的生物鐘是顛倒的,白天睡得昏天黑地,一到晚上就精神抖擻。我幾乎沒睡過一個超過兩小時的整覺。喂奶、換尿布、拍嗝,一套流程下來,剛躺下沒多久,她的小嘴又開始到處尋找。我的乳頭被吮吸得皸裂,每一次喂奶都像上刑。
下午三點,安安又毫無徵兆地哭了起來,聲音嘹亮,穿透力極強。我掙扎著從床上坐起來,刀口傳來一陣尖銳的刺痛,讓我倒吸一口涼氣。我抱起安安,笨拙地拍著她的背,輕聲哼著不成調的歌。
「又哭了又哭了,煩不煩啊!」
張偉推門進來,臉上滿是不耐煩。他沒戴耳機,顯然是被哭聲打斷了遊戲。他看了一眼我懷裡哭得滿臉通紅的女兒,眉頭皺得更緊了,「你就不能讓她別哭了?吵得我頭都疼了。」
我渾身一僵,抱著孩子的手臂有些發抖。疲憊和委屈瞬間湧上心頭,眼眶一熱,差點掉下淚來。我深吸一口氣,把眼淚逼回去,聲音沙啞地問:「你能不能過來幫我一下?我傷口疼,抱不動了。」
張偉撇了撇嘴,一臉不情願地走過來,卻沒有伸手接孩子,而是拿起桌上的水杯喝了一大口水,說:「我哪兒會抱啊,那麼軟,萬一弄傷了怎麼辦?再說了,帶孩子不都是女人的事嗎?我媽那時候生我,一個人還不是照樣帶,哪有你們現在這麼嬌氣。」
他的話像一盆冰水,從頭到腳澆在我身上。
結婚前,他不是這麼說的。那時候,他拉著我的手,信誓旦旦:「舒雅,你放心嫁給我,以後家裡什麼事都不用你操心。我賺錢養家,你貌美如花。有了孩子,我肯定是個超級奶爸,換尿布、喂奶,我全包了!」
那些誓言還言猶在耳,可眼前這個男人,卻陌生得讓我心寒。
我咬著嘴唇,沒再說話,只是默默地調整姿勢,想讓安安舒服一點。可她像是知道我的無助,哭得更大聲了。
張偉的煩躁達到了頂點,他猛地把水杯往桌上一頓,發出「砰」的一聲悶響。
「林舒雅,我跟你說,這孩子是你生的,你就得負責帶!誰生的誰帶,天經地義!你別指望我,我白天上班那麼累,回來還得聽她哭,我早晚得被你們娘倆逼瘋!」
「孩子誰生的誰帶。」
這七個字,像七根燒紅的鋼針,狠狠地扎進了我的心裡。
我愣住了,懷裡撕心裂肺的哭聲仿佛都離我遠去了。我看著張偉,這個我愛了五年,決定託付一生的男人,他的臉因為煩躁而微微扭曲,眼神里沒有一絲對我和孩子的憐惜,只有被打破了安逸生活後的憤怒和厭棄。
原來,在他心裡,孩子只是我一個人的。生孩子是我的事,養孩子也是我的事。他,只是一個提供精子的「局外人」。
我忽然想笑,喉嚨里卻像堵了一團棉花,發不出任何聲音。
我低下頭,看著懷裡哭得上氣不接下氣的女兒。她的眼角掛著晶瑩的淚珠,小小的身體在我懷裡不停地抽動。一股巨大的悲涼和憤怒,從我心底最深處猛地竄了上來,瞬間席捲了我的四肢百骸。
好,張偉。
這是你說的。
誰生的誰帶。
我記住了。
我不再看他,也不再試圖與他爭辯。我抱著安安,輕輕地搖晃著,用盡全身的力氣,擠出一個溫柔的聲音:「安安不哭,寶寶不哭,媽媽在呢。」
奇蹟般地,安安的哭聲漸漸小了下去,最後變成了小聲的抽噎,在我懷裡睡著了。
張偉見孩子不哭了,大概覺得自己的「威懾」起了作用,滿意地哼了一聲,轉身又回到了他的遊戲世界裡。
房間裡恢復了死一樣的寂靜,只剩下我和女兒均勻的呼吸聲。我抱著溫熱的、小小的她,身體卻感覺一陣陣發冷。
那一刻,我心裡某個地方,好像徹底碎掉了。
第2章 一個安靜的決定
接下來的幾天,我和張偉之間陷入了一種詭異的沉默。
他照常上班,下班,打遊戲。我照常喂奶,換尿布,在無盡的疲憊和傷口的疼痛中掙扎。我們住在同一個屋檐下,睡在同一張床上,卻像是隔著一條無法逾越的鴻溝。他不再抱怨孩子吵,我也不再向他求助。
那句「誰生的誰帶」像一根毒刺,深深地扎在我心裡,每一次呼吸都會牽扯到,泛起密密麻麻的疼。
我媽王秀蘭每天會過來給我送飯。她看著漸憔悴的臉和沉默寡言的樣子,眼裡滿是心疼。
「舒雅,是不是跟小偉吵架了?」她一邊把保溫桶里的鯽魚湯倒出來,一邊小心翼翼地問。
我搖搖頭,扯出一個比哭還難看的笑容:「沒有,媽,就是累的。」
我不敢告訴她。我怕她擔心,怕她去找張偉理論,把事情鬧得更僵。這是我自己的婚姻,我得自己處理。
王秀蘭嘆了口氣,沒再追問,只是默默地幫我把安安的髒衣服拿去洗,又把房間收拾得乾乾淨淨。她臨走前,拉著我的手說:「舒雅,月子裡可不能哭,傷眼睛。有什麼事別憋在心裡,跟媽說。要是小偉欺負你,你告訴爸,你爸饒不了他。」
我點點頭,眼淚卻在母親轉身關上門的那一刻,無聲地滑落。
我不是在哭張偉的冷漠,我是在哭自己曾經那個關於婚姻和愛情的美好幻想,碎得一地狼藉。
夜深人靜,張偉在客廳打遊戲的鍵盤敲擊聲,和身邊安安均勻的呼吸聲交織在一起。我睜著眼睛,毫無睡意,腦子裡反覆迴響著那句話。
「誰生的誰帶。」
是啊,孩子是我生的。十月懷胎的辛苦,是我一個人承受的。分娩時撕心裂肺的疼痛,是我一個人經歷的。現在,產後恢復的艱難和日夜顛倒的勞累,也是我一個人的。
那我還要這個所謂的「丈夫」做什麼呢?
他只是一個同住的房客,一個孩子的「基因貢獻者」嗎?
我摸了摸安安柔軟的頭髮,一個念頭,像一顆種子,在我心裡悄悄地破土而出,並且以一種瘋狂的速度生根發芽,長成了參天大樹。
這個念頭讓我自己都嚇了一跳,但隨之而來的,卻是一種前所未有的平靜和堅定。
第二天,我趁著張偉去上班,給我爸林建軍打了個電話。我爸是個退休的中學老師,性格沉穩,不愛多言,但向來是我最堅實的後盾。
電話接通,我爸熟悉的聲音傳來:「喂,舒雅?」
「爸,是我。」我的聲音有些發緊。
「怎麼了?是不是身體不舒服?還是安安怎麼了?」我爸的語氣立刻緊張起來。
「沒,我們都挺好。」我頓了頓,深吸一口氣,說出了那個盤旋已久的決定,「爸,我想給安安上戶口。」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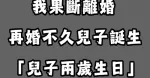
 武巧輝 • 3K次觀看
武巧輝 • 3K次觀看
 楓葉飛 • 2K次觀看
楓葉飛 • 2K次觀看









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