這兩個字像兩把冰冷的錐子,狠狠扎進莊鐵山的心臟。
他臉上那點剛剛復甦的神采,瞬間灰敗下去,凝固成一種死寂的蒼白。
伸出的手指還僵在半空,指著那塊他精心挑選的、最適合做紅燒肉的五花肉。
他看著兒子,眼神里的光熄滅了,只剩下巨大的震驚和一種被徹底碾碎的痛苦。
原來,他小心翼翼的存在,他試圖靠近的努力,他唯一能想到的表達愛意的方式,在兒子眼裡,只是「添亂」。
他在這個家裡,不僅多餘,而且是個麻煩。
他緩緩地,極其緩慢地放下手,低下頭,看著自己那雙布滿老繭、指甲縫裡還嵌著洗不凈的泥土痕跡的大手。
這雙手,曾經撐起整個家,曾經為他遮風擋雨,曾經做出他咂嘴回味的美食。
如今,卻只配得到「添亂」兩個字。
所有的堅持、所有的忍耐、所有離鄉背井的孤獨和格格不入,在這一刻,轟然倒塌。
長途跋涉的疲憊,城市生活的窒息,無所適從的惶惑,想做點事卻總搞砸的自責,無人可說的寂寞……所有積壓的委屈和心酸,如同冰封的河面在瞬間炸裂。
但他沒有爆發。
只是抬起頭,眼神空洞地看著兒子,又仿佛透過他看向很遠的地方。
他的聲音異常平靜,卻帶著一種斬釘截鐵的決絕,一字一句地說:
「別留我。」
「我這就走。」

說完,他轉過身,不再看兒子瞬間錯愕的臉,邁著異常沉穩的步伐,徑直朝菜市場出口走去。
他那挺直的、微駝的背影,在嘈雜的人群中,顯得格外孤絕又無比堅硬。
莊磊愣在原地,手機又響了起來,他卻像沒聽見一樣。
父親那句話,每個字都像錘子砸在他心上。
他看著父親決絕離去的背影,第一次清晰地意識到,他可能真的要失去他了。
他慌忙追上去。
「爸!爸!您去哪兒?我不是那個意思!」莊磊追上父親,一把拉住他的胳膊,語氣焦急又帶著懊悔。
莊鐵山停下腳步,卻沒有回頭,只是用力,一根一根地掰開兒子的手指。
他的手像老樹的枯枝,卻蘊含著不容置疑的力量。
「鬆開。」他的聲音依舊平靜,卻冷得像冰。
「爸,我錯了!我剛才那是急糊塗了,工作上有點事,我胡說八道的!」莊磊急得語無倫次,周圍已經有人好奇地看過來。
莊鐵山終於緩緩轉過身,看著他,眼神里是莊磊從未見過的疏離和失望。
「工作的事,是大事。」他頓了頓,聲音低沉,「我,是小事。給你添亂了。」
「不是的,爸!您看我這張破嘴!」莊磊急得想抽自己,「咱回家,回家再說,行嗎?我給您賠罪!」
「家?」莊鐵山重複了一下這個字,嘴角扯出一絲苦澀至極的弧度,「那是你的家。我的家,在莊家屯,有炕,有灶台,有我能碰、能摸、能『添亂』的東西。」
他不再多說,掙脫兒子,繼續往前走。
莊磊只能像丟了魂一樣跟在後面,一遍遍道歉,解釋,保證。
但莊鐵山仿佛什麼都沒聽見,只是堅定地朝著一個方向走——汽車站的方向。
第五章:無法彌合的鴻溝
莊磊最終沒能把父親拉回家。
在那個嘈雜的汽車站,莊鐵山用他帶來的所有錢,買了一張最早回縣城的班車票。
莊磊要給他買更舒適的快客車票,被他拒絕了。
要給他錢,他更是一眼都不看。
「我能把自己接來,就能把自己送回去。」這是他上車前說的最後一句話。
班車噴著黑煙,搖搖晃晃地開走了,載著那個固執、傷心、卻維護了最後尊嚴的老人,消失在城市的車流里。
莊磊失魂落魄地回到家,面對妻子擔憂的詢問,他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
那個父親坐過的陽台,空蕩蕩的,卻仿佛充滿了無聲的譴責。
他精心構建的「孝心」大廈,在這一刻,徹底坍塌成了一片廢墟。
他以為自己給了父親最好的,卻從來沒問過,那是不是父親想要的。
他以為接來享福是終點,卻沒想到,這成了父子間最深鴻溝的起點。
那八個字,像一把刀,斬斷的不僅是當時的溫情,可能還有父子間最後那點脆弱的連接。
有些東西,碎了,就再也拼不回去了。
孝心若只流於物質形式,便成了溫柔的綁架。
尊嚴是老人融入陌生世界的最後底線,一旦戳破,裂痕難補。
最深的孤獨,是至親環繞卻無人讀懂你的世界。
真正的享福,或許不是給予,而是理解和尊重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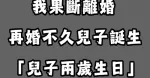
 武巧輝 • 4K次觀看
武巧輝 • 4K次觀看
 楓葉飛 • 2K次觀看
楓葉飛 • 2K次觀看









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