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你們二人倒是交心得很,什麼事情都同他說。」
慕瀟策立刻打斷了他的話。
「紅口白牙地汙衊自個兒的夫人,你倒也算是男人中的頭一個了。那蘇荷當街要你做選擇,你毫不猶豫地當著眾人的面答應了同雲錦和離的事兒,你自個兒都忘了?雲錦三歲會詩,五歲能舞,七歲寫得一手好字,便是你父親都讚嘆有加。娶到了名震京城的才女,是你三生有幸!你竟還不知珍惜,當眾羞辱!」
江敘白竟被這段話逼得後退了幾步。
他實在難以辯駁,只能衣袖一揮,轉身負手不再看他。
「這是我們夫妻之間的事情,與你無關。個中緣由我已經同雲錦說清楚了,她會理解你的。」
江敘白錯了,我實在無法理解。
哪有自家夫君為了哄旁的女子安心治病,找髮妻假意和離的道理。
若是這事兒都能做,那二人之間的情意又算得了什麼呢?
上一世,我就是因著這份不理解,所以沒有鬆口答應這個荒唐又無理的要求。
蘇荷拒絕治療,活生生地拖死了自個兒。
江敘白恨透了我,同我開啟了漫長的冷戰。
才會在我陷入險境之時,認為是我求和的手段。
讓我屈辱地死去。
這一世,我便隨了他的心意。
4
「他同你說了些什麼?」
慕瀟策走後,庭院中只剩下我們二人。
我搖了搖頭。
「沒什麼,不過是溫習了一番我的近況而已。」
大抵是想到那日當街逼我和離的場景,他的語氣有些躊躇。
「那日的事情,是未曾考慮不周全。只是好不容易尋來的神醫,若不能安撫蘇蘇答應配合,恐怕就留不住人了。」
「我應當私下同你說的……」
太傅之前有位摯友。
滿腹經綸卻生性喜愛自由,不願入朝為官。
妻子去世後,帶著女兒回到了京城,暫住在太傅府中。
江敘白十分欽佩,拜了對方為師。
直到對方去世,將女兒託付給了他多加照拂。
這女兒,便是蘇荷。
蘇荷對江敘白的依賴,讓我隱隱覺得有些不對勁。
我曾問過他。
他有些不悅,卻還是耐著性子解釋。
「蘇蘇生母走得早,自小身子又弱。師傅走後,她能倚靠之人,也只有我了。故此稍微患得患失了些,倒也不能怪她。」
「師傅臨終所託,我定是要擔負起照拂她的責任才是。你且放心,在我心中,她就如同我的親妹一般。」
「我的心裡,只有你。」
我信了。
跟小時候一樣,不管江敘白說什麼,我都深信不疑。
甚至,我還想著同江敘白一起,肩負起照拂她的責任。
直到我發現她對我的敵意頗深,我才沒有再試圖同她親近。
可我從未干涉過江敘白對她的照拂。
直到她哭訴著不想獨自住在太傅府里。
「江哥哥如今有了自個兒的宅子,自老大人過世之後,我便獨住許久,實在害怕得很。江哥哥,你是不是同父親一樣,也要丟下蘇蘇一人……」
可自從我們成婚後,江敘白便日日回去看她。
一日三頓餐食,總是有一餐陪著她用的。
面對著她的哭訴,江敘白心軟了。
試探性地問我,能不能將她接到我們的府邸之中。
看著他眼中的祈求,我答應了。
可入府之後,蘇荷因著對花粉過敏大病了一場。
滿院為我種下的梨花樹,被江敘白親手砍斷。
包括大婚那日,我們二人親手種下的那棵。
「左右還是給你留下了棵,蘇蘇體弱,你作為嫂嫂,大度一些。」
這次,他沒有同我商量。
只是在我回府看到這滿地狼藉之時,輕飄飄地告知了我一聲。
再到後來,江敘白花費重金替蘇荷請來了西域有名的神醫。
而蘇荷卻當街提出。
「要我配合神醫治病,江哥哥你要同曾雲錦和離我才肯!」
我倍感荒唐,江敘白卻一口答應了下來。
他還是那套說辭。
「蘇蘇身子不好,對我占有欲強了些。待她身子好起來之後,便不會再這樣了。你是嫂嫂,大度些。」
這些話,是他低聲附在我的耳邊說的。
只是對我一個人的安撫。
而後便走到了蘇荷身邊,提高了聲音。
「你我回去,便簽了和離書。」
他看向蘇荷,面色溫柔。
「蘇蘇,這樣能乖乖配合神醫的治療了嗎?」
蘇荷乖巧地點了點頭。
5
見我不做聲,江敘白驀然提高了聲音。
「為何不搭話?還在彆扭嗎?我都同你解釋了,為何你還要苦苦相逼?!」
我苦苦相逼?
明明是他在逼我啊。
江敘白往日最是在意我。
小時候,他會在我策馬狂奔的時候,阻擋父親對我的說教。
「誰規定的女子不能肆意策馬的?雲錦就應當活得肆意才是。」
成婚後,他會在我提出不想住在昔日的太傅府的時候,購置宅子,而後站在我的身前。
將那些「不孝順、沒心肝」、「心比天高,女子家家的,不住婆家的宅子,還想住在哪裡去?」的流言蜚語,通通替我擋住。
「我娶妻回來,是疼惜呵護的。她若是不想,便在購置一處宅子便是了。哪裡來的道理,非要固定在一個居所?」
就是這樣的一個人,在不過區區三年的時間裡,忘記了之前的一切。
現如今,他只想讓我乖乖聽話。
同他假意和離,安撫蘇荷。
再同以前一樣,沒名沒分地跟在他的身邊。
等到他的蘇蘇身子治好。
他厭惡了我的肆意自由,不願我再有自個兒的思想。
只想將我變成一個以夫為天的傀儡。
他自個兒都沒察覺到,他對蘇荷的照拂,早就超過了正常的範圍。
遭受了上一世的苦楚,我早就在心中將他放下。
可難免的,心裡還是會泛起一陣委屈。
見我眼中升起了濕意,他愣了愣。
隨即,便將情緒收斂起來,顯得更不耐煩了些。
「哭哭哭,成日就曉得哭。往日怎的不知,你怎麼愛掉眼淚?!」
「雲錦,自小到大,我可曾虧待過你?你待你不好嗎?你要什麼我便給你什麼,處處站在你那頭。可你呢?我只不過是想完成師傅的遺願,替他照拂好唯一的女兒。你怎就不能,設身處地我替我想想呢?」
「人人都說夫妻一體,原本這恩情,你應該同我一起報答才是。可我從未強迫過你跟我一起做什麼,現如今只是讓你陪我一起做場戲,你都不願嗎?」
他看著我,滿眼的失望。
「雲錦,你何時變得如此鐵石心腸了?」
他好似忘記了我所做的一切。
從前,我百般對蘇荷親近。
可她卻對我帶著滿滿的敵意,我一靠近她,她便哭。
我特意替她尋回來的頭面,被她「不小心」摔碎。
她不過是隨意提了一嘴那料子好看。
我便專程託人從江南運來,送給她做衣裳。
她卻將那布料做了件小衣服,穿在了看院的大黃狗身上。
我做的,難道還不夠多嗎?
眼前這個一旦涉及到蘇荷的事情,便喪失了全部理智的人。
早已經不是我記憶中的那個江旭白了。
我苦笑一聲,抬手輕拭面上的淚意。
剛想開口,便被一道虛弱的聲音打斷。
「江哥哥,若是嫂嫂不願的話,就算了。莫為我,傷了你們二人的和氣。」
6
蘇荷靠在院門外,用手捂著胸口,面色蒼白。
江敘白見此,忙迎了上去。
「你不好好在自己的院子待著,怎麼過來了?」
「這院裡還有一棵梨樹未砍,你過來會受不住的。」
蘇荷拂去了他試圖攙扶的雙手,滿眼倔強。
「我這身子,就這樣了。高低是治不好的,不如早些去同父親團聚。」
江敘白皺眉打斷了她的話。
「胡言!我已替你請來神醫,你怎麼會治不好?」
「乖乖回去躺著,我待會兒便帶著和離書過來尋你。你看到之後,就能安心配合治療了,對不對?」
蘇荷撐著自個兒,抬腳朝我走來。
「向來嫂嫂是不願意的。江哥哥,我知道我對你依賴了些,所以不招人歡心。可我只是太害怕自己一個人了。神醫說過,也不一定有把握將我治好。我只是想有一個人,完完全全地屬於我,這樣我死了,便沒有遺憾了。往日我還有父親,可如今,我只有你了。」
蘇荷緩慢地走到我跟前,朝我跪了下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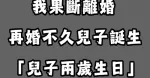
 武巧輝 • 2K次觀看
武巧輝 • 2K次觀看
 楓葉飛 • 1K次觀看
楓葉飛 • 1K次觀看




















